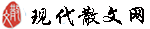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Ͱͽ����������ĸ�e
��������3�r���҂���һ���ČW(xu��)���ͽ������ĸ�e�� ���A���x�^�Ĵ�d�һ��һ��������ɷ�˹��������������������ĵ��Ę��£��@�ǰ�����ǰ��۵����������{(di��o)����ͻ��֎����o�ޱ������������ݲ�����ؑѣ����^һ�������o(j��)�����ˣ����������ڻ�tɫ��õ�廨���У���������ǰ��۵��r���������N�����ɫ�������л�һ�����S�ļ��飬���o�����ֵĴ��҂��������˾�(qi��ng)�������Ը� ��ŮС�֡�С����֪���H��ǰ����Ȥ��������101��tõ�����ɾ�ġ��ġ��Σ��[���ڰ��ϰ������Ļ���ǰ�����ϵ��z���x�õ���һ��1995��z�ں��ݵIJ��գ��@�ǰ�����ǰ�ܝM���һ������Ƭ�ϵ���һ���tɫ�A��������(c��)����ȻЦ��Ц�ݜ�ů��������һ��������Ę�ϵĺ���ꖹ⡣�ڲ��õ����Ÿߝ��������������`���һ�r���X���ϲ������h(yu��n)�x��˹��˹�ԡ�˹��˹�Ќ������݅�����ң���ů�����粻����ğ��� ��ͨ�� һλ���ң�����һ������ ��e�xʽ����3�c(di��n)�_ʼ��Ȼ����(d��ng)ӛ��2�c(di��n)�s�����A���x�^�r���l(f��)ǰ�������Ⱥ���ѽ�(j��ng)�ų��ˎ�ʮ���L�(du��)���`���⣬����M����������(li��n)��Ψ��һ�И��صĺڵװ��֡���ͽ��������С����@�ݘ��������������ǰ���صĞ��ˡ������ߝ����`�����ǿ����W�q������һ������Ը���^����һ������ͨͨ�ĺ��ˡ� ��e����Ⱥ�У��кͰͽ���ʮ�꽻��������ѣ�������(j��ng)����϶�����t(y��)�o(h��)�ˆT���Џijɶ��h(yu��n)��������С�W(xu��)���������S�����_�����������ȡ��W�l(f��)����˪ѩ�Ĵ������ߡ����S�����s���h(yu��n)��·�^����ֻ�����@������������o�����p�p��һ�������@�����F�����\���������һ�ۣ�Ը���ߺá� ��������䣬����o(h��)�������������8��֮�ã���1994�굽20 02�ꡣꐰ�����ӛ�ߵİ���Ȧ�У�����Щ�ִ٣�����������֪�fʲô�á���(d��ng)�������u�r�����еİͽ�r��ꐰ��������ˣ����@���������f���ҬF(xi��n)��������IJ�֪���fʲô�źã���Ҳ���y�f����Լ��F(xi��n)�ڵ����顣��ꐰ����f���Լ��ڰ�����߅������@ô���꣬���ڌ���������ǂ��ͽ�����֪�ıȄe��֪���ö��S�࣬�������ˣ����X���������������õ��ǂ������ˡ��������ĕr����ô�H�У���߀���fԒ�ĕr����߅�oՓʲô�˶���(d��ng)�Լ�С݅���������� ���н���ε���@λ���ݽ̎������ѽ�(j��ng)80���g�����_���á����������֟o���������ЄӸ�����������䌍(sh��)�Ͱ�������ƽ����ֻ�Ǐ��������װl(f��)��һ·�x�����ϵĕ��߁����ġ��ҡ���������������F�����꡷��늡����ġ���ҹ�������S��䛡�������������ס�Ϻ���W(xu��)�������������Ǫ�(d��)�ԔD���F�s�����A���x�^�����f���ڰ��ϲ��ؕr�������״�ȥ�A�|�t(y��)Ժ̽ҕ���ڰ�����������Ҳ��ȥ�俵·113̖���Ͼ������䣬��˲��o����ֻ��?y��n)飺���ͽ���һ�������ң�һ���f��Ԓ�ĺ��ˣ����������� ���dzɶ�����ͨ혽�С�W(xu��)��һ�����꼉�W(xu��)������ǧ����������ͬ�W(xu��)�۵�ǧ���Q�͵������`ǰ��ǧ���Q��õ��t�ļ��۳ɣ��������U�P���������ͽ𠔠����ߺð�Ϣ�ɡ���һ��Ҫ�����W(xu��)��(x��)�����f��Ԓ��Ҫ�f��Ԓ���úÌW(xu��)��(x��)�����@�����꼉�W(xu��)�����Vӛ�ߣ������W(xu��)У��УӖ(x��n)���ǣ����f��Ԓ�������ˡ��� �������Գɶ������ɶ��̈�(b��o)���M����24�˵ġ��ɶ��F(tu��n)�����F(tu��n)�T����С���DŽ��^ʮ�q��С�W(xu��)���������L����74�q�����a�⣬���ϲ��ڰ���߀���ڕr�������Ϻ������ף�ۡ����ɶ��F(tu��n)���Ѱ�ɽ��ˮ�g��˼����Ϻ���24�����`���������˾���{(l��n)ɫ�M�������������ߺã����l(xi��ng)���������㡣�� ���Џ����������һ����(li��n)�̈́e���ϣ����ٚq��ҹ���c(di��n)�����`���������o(j��)�ČW(xu��)���������V�Ҍ�(sh��)��������������Ǐ��¹��������ģ��֮����^�ǘI(y��)���dȤ�������@���Ͱ������һ�̣������Ա����⣬ǰһ���Bҹ�����@����(li��n)���@Ҳ����������İ��ϡ��� ���з��o��40����ǰ��1963�꣬���ǵ����t(y��)ˎ�̵�ĠI�I(y��)�T����ȫ����ģ������ʒɺȥ���L�����Ĵ��_ʼ�����Ͱͽ�һ�ҵ����x���������俵·�ļ����ȥ�^�ܶ�Σ���סԺ�r����߀����ȥ�������F(xi��n)�ڣ������ˣ�����һ�����������ˡ��������o�f������̎�㲻�����Z��ֻ���߳��`�ú�(d��)��ĬĬ���ۜI������Kaul Nussmueller��ӛ�߶�����ЩԌ����һ��41�q�ĊW�����˕����F(xi��n)���@����䮔(d��ng)���_�ڕr��Ԓ�Z�g��¶�����Ƿ����飺����֪���ͽ����Ї���������ң��������p�r�����x�^���ġ��ҡ�������������ұ���������ӿ�ӵļ���͟��������ӡ��mȻ�Ҳ����Ї��ˣ��������X�ðͽ���x�Ҳ����b�h(yu��n)���������֡�������Ʒ����ȫ���{�ڇ��硢�Z��֮�ϣ����ǂ�����ġ����F���ˡ���������ϧ�������^���� ͨ���`�õ�·�ϣ��̶̵�50�A���������״����҂����ϵĻ�Ȧ���p�����e���܌���һ������Ϥ�����֡��Ї����f(xi��)14λ����ϯ�R�R���F(xi��n)�����A���x�^��������С� 2�c(di��n)���^�r��ӛ�߱㿴��ꐴ���������һ��һ�����`�����߳����߶Ƚ�ҕ�ֳ����ܲ�ʹ֮����������߲����p�ɡ������ԣ�����Ĉ������ČW(xu��)����겻�����F(xi��n)�ġ������룬�˿́����@����������������Ƶģ���Ȼ��
���P(gu��n)��x:
|
�x���@ƪ���º���������Σ�
|
�W(w��ng)���uՓ������ 0 �l�uՓ�� |
ɢ����Ϣ
| ��������ؔ(c��i)�� | �O������x | �á��z·ɢ | ���ɢ�Ľ��� | ||||
| ���6λ���ҫ@ | �Zƽ����ɢ�� | ���O���ČW(xu��)�� | ���������ļ� | ||||
| ˡ��ֱ��--�� | Ԋ�������е� | ɢ�ĵČ��� | ��Ȼɢ�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