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玉江工作照片
祁玉江(以下簡稱祁):陜西省志丹縣縣委書記
王春(以下簡稱王):中國散文網編輯
(題記)
去陜北,有緣和志丹縣縣委書記有過不到半個小時的聊天,我們前一天住在縣城,看了由他一手打造的美麗的夜景,體會著小城安靜恬美的氛圍,走過小廣場上休閑散步的人們,聽著一些人對書記的欽佩之語。當天晚上他接待重要來訪,我們在飯桌上時他舉著酒杯來歡迎,性情熱烈。第二天臨近中午才終于有了時間一行人和他坐下談事聊天,,采訪只是進行了一小段時間,很充沛,但不過癮,書記說,時間太少了,要是有時間,我想說的多著吶。看著這個激情主義的充滿責任心的人,有能力的人在能力之外,體力總是強大的。我們握手,說兩句閑話,他又神采奕奕去忙別的事情去了。文學于他,就是這樣的日子中不可缺少的溫柔和開闊,他自己,也是把工作和文學都一樣做到溫柔和開闊。
 祁玉江在第四屆全國冰心散文獎頒獎大會上
祁玉江在第四屆全國冰心散文獎頒獎大會上
王:書記你好啊,您是散文寫作者,已經出版了九本散文集。這次是在中國散文網上做一個有關您的專題,請問您平時經常上網嗎?
祁:很少,因為太忙,沒有時間,但我會讓工作人員利用網絡替我查閱資料。
王:你是太忙了,這兩天目睹了你工作的螺旋狀態,但看您游刃有余,生機勃勃。我想問的是,寫了這么多的文章,時間呢?怎么抽出時間?
祁:晚上,節假日有些時間。
王:我看您昨天晚上回去應該半夜了吧,每天晚上九、十點能回去嗎?
祁:基本不行,要再晚一點了。
王:那寫作就是半夜。
祁:是啊,一兩點鐘,不過我時間少,但我筆頭很快,很多東西都已經裝在心里,就等著下筆噴薄而出了,寫一篇差不多字數的散文最多三個小時就好了。
王:內心的感受已經很充足了。每天這樣的日程,您不感到累嗎?
祁:這是個狀態問題,精神上很喜歡某個事情,很投入,是不會累的,累也是享受在其中的感覺。我這個人一直比較積極,摯愛著工作和寫作。真的是把我的工作當做幸福,把解決矛盾和問題當做挑戰和樂趣,把自己的創作當做最大的支柱,所以,骨子里愛什么,就能某種程度上獲得隨心所欲的自由度,不覺得累。
王:沒時間休閑娛樂啊。
祁:我當然也玩,和朋友們啊,我玩得很瘋的,哈哈,就是機會少,每天只要有時間,要騰給讀書寫作。
王:我想您玩的時候肯定也很盡興。
祁:我是性情中人,我愿意過一種閱歷豐富、經歷豐富的生活。年幼少年的時候受苦長大的,在大山里摸爬滾打長大,當時覺得苦,現在想想真是一筆財富,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礎,和文學的根。
王:是啊,我看你的散文集,很多書名都和“路”有關,比如:《山路彎彎》、《心路歷程》、《征途漫漫》、《一路風塵》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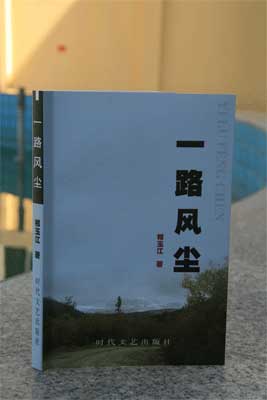 《一路風塵》2006年6月時代文藝出版社
《一路風塵》2006年6月時代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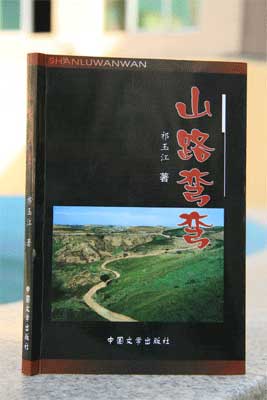 《山路彎彎》2002年5月中國文學出版社
《山路彎彎》2002年5月中國文學出版社
祁:我覺得我一直是在路上,是一個趕路者,朝著更好的方向,走過來的路一點一滴都在我內心發酵,生發出沉淀出清香的情緒。
王:說明您首先是一個非常細膩和重感情的人。
祁:文人肯定是細膩的,往往看到一片葉子,現在是春天,看到發芽看到花開,看到一個小小的細節,心里就不只是這個細節,聯想和觸動很多,心里反復映照出很多東西,就要把它寫出來,一吐為快。
王:生活處處皆文章。
祁:那天吃了一碗仡佬面,我寫了一篇文章,一碗粉湯,今天見到誰,包括咱們的聊天,我可能都會寫出文章。
王:寫作讓生活重新布局了一番,并且更加用心。您很愛讀書,都讀哪方面的書?
祁:我看書興趣比較廣泛。第一類就是文學書,最近幾年出版的好的長篇小說都讀,《古爐》前不久看完。
王:真是佩服,您時間這么少,還有時間讀長篇小說。
祁:每天規定自己讀20頁書,堅持下去是很可觀的。外國名著現在也重新讀,每個年齡都會有新的理解。
王:散文呢?喜歡那些作家?
祁:也讀了很多。王宗仁的散文我很喜歡,賈平凹的,散文很極致。還有和谷的、王劍冰、周濤等等,好散文越來越多。
王:還讀很多其它領域的書?
祁:歷史方面的,世界歷史,中國歷史,明清的,還有個人傳記。我還喜歡天文地理,自然科學。研究研究星星什么,呵呵。
王:怪不得書記給志丹的山上掛滿了星星,我們昨天去看了夜景,非常美麗,您是現實主義加浪漫主義。
祁:多了解宇宙、星辰,會明白人類的渺小,在宇宙中,比灰塵還不如,人的一生就是一個過程,所以要珍惜這個轉瞬即逝的過程。
王:因為您從事著忙碌的行政工作,要管理一個縣的方方面面,雖然在這幾年,大家有目共睹志丹的顯著變化,但我們都知道成績的后面有很多艱辛的東西,您又是一個有著文人情懷的浪漫者,這看來好像是沖突,您內心有痛苦的時候嗎?
祁:不可能全是美好。有痛苦、也碰到威脅,還有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覺得一個人只要內心的力量足夠強大,君子坦蕩蕩,自信,善于快速調整,就沒有什么能難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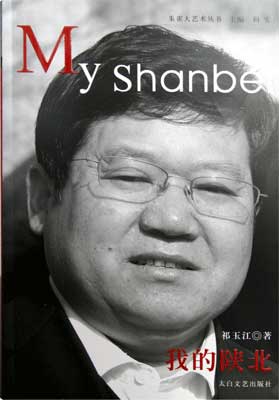 《我的陜北》2008年5月太白文藝出版社
《我的陜北》2008年5月太白文藝出版社
王:通過接觸您,我覺得您確實是一個自信的人,因此覺得很陽光。那么,行政工作和創作這之間的關系應該怎么擺呢?怎么處理?
祁:其實都是相輔相成的。生活本身是創作的源泉,我的作品中,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寫工作的事情,或者是在工作中碰到接觸到的很多東西,工作先有體會,寫作是總結,這個反思因此又推動了工作,這一切有和路有關---“我從紅都大地上走過”。
王:您的文章都是真實的。
祁:是的。我都是紀實性的散文,純粹是真的,是生活,我不需要虛無縹緲。
王:這樣的東西因為可貴的真是,讓人讀起來很入心。
祁:是的,比如我寫一個下鄉總能碰到的智障人士九斤,已經把生活給他安頓好了。我寫的那篇《九斤》,很感人。
王:對于您的散文風格,您自己怎樣評價?
祁:我覺得我達不到藝術的高度。但是我體現了生命力,寫實的東西感染力強。
王:寫的時候一定是投入的,很享受的。
祁:你打動不了自己就打動不了別人。前不久寫父親的文章,我自己寫的時候就忍不住流淚讀者看的時候才能感覺真情。
王:我能想象您半夜萬籟俱靜的時候,一個人卸下了白天的西裝革履,一支筆,一個臺燈,全然沉浸在另一個世界的氛圍。聽您的工作人員說,您平時對于來信每封都回?
祁:是啊,這是一種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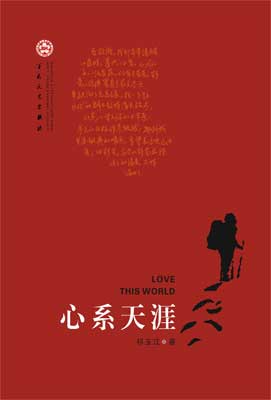 《心系天涯》
《心系天涯》
王:工作真是夠忙的。您的寫作計劃也很難保證吧。
祁:對于日程,我是保證有一個大穩定小調整,隨時調整。
王:我們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感覺,就是剛一進志丹縣城,非常干凈,沿路過來,這是很明顯的。知道您堅持上街親自帶頭撿垃圾好幾年了。
祁:我不是愛走路嘛,每天中午晚上走在縣城街上,就會順便撿撿。
王:評上國家衛生縣也是名副其實的。您這個方法好,不用說話,不用嚴管,自然大家都步您的后塵,受您的影響了,呵呵,書記都撿垃圾,誰敢扔?
祁:這是以身作則,也是一種影響嘛。
王:還有一點,我發現街上的出租車司機都和您的裝束一樣,西服領帶!
祁:這是一種形象,很重要。
王:就是西服料子不如您的吧,呵呵。
祁:還有一點,我每天記日記,一天不斷。
王:每天?
祁:是的。從2007年7月7日來這里,一天未斷。記一記今天做了什么工作,發生了什么事。其中還有一年我另外還同時記了一本有關生活感悟的日記。這兩本志丹日記,經過整理也將出版。
王:這是很生動的記錄。美國有個女作家說,寫作者讓生活重現,等于又活了一回。聽說您給大家講課非常受歡迎?而且內容比較廣泛?比如怎樣度過人生?我覺得特別好。
祁:是的,我講講做人做事,政治形勢、經濟問題,還有倫理道德方面,對于政府工作人員,這些都是提高素養的必要。
王:除過寫作,您還有什么樣的業余愛好呢?
祁:多啦,我喜歡打乒乓、愛唱歌、旅游、跳舞等等。
王:看來只有以后退休后全面發展啦,創作上有計劃嗎?
祁:計劃要寫一部20歲之前在鄉村的生活,長篇散文。還要寫一個《問心有愧》,把我這么多年內心深藏的歉疚啊等等呈現出來。
王:會寫小說嗎。
祁:會寫,已經有腹稿。有關70年代。
王:現在有一種“官員寫作”的說法,您怎樣看。
祁:我覺得只是一種說法而已,寫作不分身份,寫作能力是一種很重要的能力,我覺得恰恰缺少領導寫作。
王:對于志丹的文學事業,您支持非常多。
祁:是的,我不能只是自己寫,我還要引領大家,準備辦“文學講習班”,還要搞采風活動,發現更多的文學人才。
王:您時間有限,但我們聊得很愉快。
祁:是啊,要是有更多時間,我的話題還多著呢。
王:這么多年來的路,您覺得內心達到您要的狀態了嗎?
祁:我告訴你,我是吃苦長大的,原來的職業夢想就是,能夠當上老師,穿上干凈衣服。現在早已超出當年的理想,我會以更好的狀態一直走下去,對得起自己的內心。
王:希望我們都能夠以文學作為證明。
附:祁玉江文學創作簡介
祁玉江,男,漢族,中共黨員。陜西省子長縣人,1958年2月生,現為中共志丹縣委書記。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自幼酷愛文學,參加工作后筆耕不輟。近年來,先后在《人民日報》、《中國藝術報》、《十月》、《散文》、《散文百家》、《散文選刊》、《青年文學》、《天涯》、《延河》、《美文》、《手稿》、《中國散文家》、《小品文選刊》、《西部散文家》、《安徽文學》、《陜西日報》、《西安晚報》、《延安文學》等報刊雜志發表作品百余萬字。有作品被收入《在場主義散文2009年選》、《2009年度華文最佳散文選》等選本。出版了《山路彎彎》、《心路歷程》、《山外世界》、《征途漫漫》、《山高水長》、《一路風塵》、《我的陜北》、《踏遍青山》、《心系天涯》九部散文集、工作研究文集《探索之路》和祁玉江作品評論集《玉壺冰心》。與人合著長篇紀實文學《壁上紅旗飄落照——紅都志丹紀事》。主編大型文典《志丹書庫》19卷22本和《陜北說書》。
散文《印象中的爺爺》榮獲2008年“綿山杯”《中國作家》第四屆“金秋之旅”筆會一等獎;散文《我的幾位農民兄弟》榮獲2008年度中國散文年會一等獎;散文《鄉下過年》榮獲2008年《延河》雜志散文征文特等獎;散文《二畝地》榮獲2008年度《延安文學》、《十月》雜志社聯合舉辦的“延安杯”全國文學征文散文獎;2009年4月,散文《大上海》榮獲當代檢察文學研究會、《檢察文學》雜志社主辦的首屆“金劍文學獎”;散文《陜北的山》榮獲2009年8月由中國西部散文學會舉辦的首屆中國西部散文獎單篇散文詩獎,并被選為陜西省2009年中考語文試卷閱讀篇目,占18分;散文《常思母親教導》榮獲2009年度《中國散文家》雜志社舉辦的“潔達杯”“愛在人間”紀實散文征文大賽三等獎; 2010年2月榮獲2009“陜西最具文化影響力人物獎”,2010年8月散文集《我的陜北》榮獲第四屆全國冰心散文獎;2010年8月散文《歸來吧,心中的精靈》榮獲第二屆中國西部散文節暨首屆中國西部大生態文學獎。
現擔任陜西散文學會副主席、西部散文學會副主席和《西部散文選刊》雜志主編。
附:代表作品欣賞
我那親愛的鄉親們
久居外地,難得回老家一趟。多年不見,鄉親們自然顯得格外親切和高興,爭著與我拉起了家常。
魏振福,當年我在鄉下的時候,是一個十多歲敦敦實實的小伙子。他本不是我們村人,是隨改嫁的母親來到我們村定居的。聽說我回來,他很想見我,卻又躲躲閃閃蹴在院子里不敢見我。當母親把他的舉動告訴我后,我喚他進屋來。他蹉著手,漲著臉,拘謹地走在我面前。沒想到眼前的他和當年的他判若兩人,僅僅是46歲的人,就滿頭銀發了。問他為什么這么年輕就白了頭?他苦笑著說:“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他的母親和繼父早年相繼去世后,因他是姊妹六人中的老大,家庭的重擔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尤其是姊妹們的婚姻大事讓他操碎了心。他不僅要為自己成家,而且還要為弟妹們操辦婚事。后來,弟妹們都已成家立業另過了,而他自己也慢慢年齡大了。眼下,二十多歲的大兒子還沒有找到對象,終日在外游蕩;小兒子在上學,還不知道將來能不能考上大學?從中不難看出,這些年來,他生活的煎熬和心頭所承擔的巨大壓力。
王崇山,當年的鄉郵員。由于多識了幾個字,“喝了幾瓶墨水”,心比天高,一次次誤過了婚姻大事,三十多歲的人了仍沒有找到對象。無奈之下,只好來到我們村上做了一寡婦的上門女婿。我高中畢業回村勞動那陣,常常與他一起趕著毛驢送糞。因我倆均算是知識分子,時不時談論歷史和國家大事,很是開心、愉快!而眼下的他,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當年一米八幾的個頭,如今矮了許多,佝僂著腰,臉上布滿了皺紋。沒想到他還是那樣的健談,一見到我就問:“今年解放不解放臺灣?”我說:“今年恐怕解放不了,但遲早會解放的!”他的眼睛一亮,說:“是呀,臺灣自古就是我們國家的領土,是當年民族英雄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回來的,應該解放!”末了,又不無擔心地說:“解放臺灣就怕引起世界大戰!”我笑了,他也笑了。我明顯地看到他牙齒脫落了不少,不禁為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境界肅然起敬!
虎娃,官民張孝峰,我兒時的伙伴。看到我在村口散步,撂下手中的擂糞镢頭,快步迎了上來。他臉膛黝黑,頭發干焦,雙眼布滿血絲,牙齒黑黃,衣衫襤褸,看上去又蒼老了許多。我伸出手要與他握手,他卻將伸出的污黑的手又縮了回去。他說他的手臟,剛抓過糞。我說沒關系。他很難為情地將手在衣襟上蹭了蹭,這才勉強地又伸過了手。這時,他老婆讓他換了衣服再見我,被我阻攔了。拉話間,他說:“聽說你在保安當了大官,前兩天我還來找你,想包一點工程掙點錢,但就是沒有找上。”轉過一個山峁,他拉著我的手,要我看他跌崖的地方。這一山崖足有二、三十丈高,七、八十度陡,一條小路從中間穿過。他說,那天下著小雨,上午九點多,他在崖畔上給牲口割草,腳下一滑,不慎摔了下去。先摔在路上沒落定,繼而又滾在溝底,頓時失去知覺。整整大半天沒有被人發現,直到下午四點多,雨點打在他的臉上,才把他驚醒。他想往起爬,可是腿像灌了鉛似的重,怎么也拉不動。他這才知道腿已經摔壞了,靠自己往上爬是無能為力了,便放聲嚎了起來,直至驚動了村里的人,才把他救了上來。而后在炕上整整躺了一年,才慢慢恢復正常。他說:“要不是老天有眼,就再也見不上你了”。我不禁為他深深地捏了一把汗!就說:“蒼天有眼,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他咧著嘴格格笑了,笑得那樣酣甜,一口黑黃的牙齒似乎也在笑,怎么也遮擋不住。
張遜平,又名張小平,乳名安則。從小喪父,早年輟學。長大后,改嫁后的母親和繼父好不容易給他成了家。然而他不務正業,游手好閑,撇下妻子和兒女,離家出走,多少年杳無音訊!后來,聽說他在外地犯了案(偷盜),被判了好幾年刑。妻子一氣之下,撇下孩子,改嫁了他人。這次,回到家后,正好碰上了他。只見他滿臉胡子,消瘦了許多。問他心收回來了沒有?他說:“到處碰壁咋能收不回來?”站在一旁的我的嫂子插話說:“安則早就務正業了,婆姨撂下的三個娃娃,大兒子已經結婚,大女兒也已出嫁,小女兒正在上學,光景過得蠻不錯哩!”安則的母親卻不以為然,一再要求我再教育教育他的兒子。而安則咧著嘴,蹉著手,只顧憨憨地笑著。
晚上,因家里來的客人較多,我就睡在隔壁鄰居二猴的家里。二猴是我兒時的伙伴,在“山路彎彎”一書中,我曾提及過他。他是一個可憐人,隨改嫁的母親來到我們村,是前面提到的魏振福的弟弟。由于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癥,留下了嘴歪耳背(聾)的后遺癥。早年他也娶過一個矮子(侏儒)婆姨。由于婆姨不能生養,他們只好撫養了別人遺棄的一個小孩,取名凱凱。后來矮子婆姨也因肝硬化去世了,留下他們父子倆相依為命。前幾年,他得了嚴重的胃病,不能下地干活,光景過得恓恓惶惶。好在經過延安兩家醫院檢查,是萎縮性胃炎,問題不是很大,這才回家休養。去年以來,胃病漸漸好轉。而凱凱卻受不了農村苦焦的生活,到外面闖蕩去了,只丟下他一人在家廄守,耕作兩坰薄地。當他敘述完這些之后,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任務似的,再不作聲了。我再問他時,他已經打起了鼾聲。不知是他苦命的一生刺痛了我,還是他的鼾聲驚擾了我,總之,我一夜伴隨著他的鼾聲幾乎未眠。
第二天起床后,與我一同回老家的侄兒祁強告訴我,全村六、七十口人走得只剩下現在的24個人了。我長嘆一聲,默不作聲。早飯后,我和四弟、侄兒祁強一同給早已作古的父親上墳燒紙。后又取道下到溝底,觀看了我的故居。我在這里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當年的三孔土窯洞門口已經塌陷,窯面也已剝蝕得不成樣子,院子里雜草叢生,山上山下的羊腸小道已經不復存在,基本上與大地連成一片。我猛然想起一位哲人說的話:“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與此同時,我也想說:“地上本有路,因為沒有人走了,便沒有了路。”下到溝谷,當年清澈的小溪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一條干溝,而且溝愈來愈深,坡愈來愈陡。看來,水土流失這些年來不但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一些地方還加劇不少!
上得山來,我又向我兒時的“樂園”和讀過小學、高中畢業回村教過書的所在地——高新莊村趕去。山上高高的寨子仿佛矮了一截,看上去并不那么雄偉了;學校空空蕩蕩,門窗破破爛爛,院子里長了不少雜草。村里幾名婦女和老頭正在鹼畔上乘涼。問學校為什么這般蕭條?他們說:“全學校只有四名學生、兩個老師,今天是禮拜天,娃娃們不上課。”正說著,迎面走來一個人,雙手拗(拄)棍,分明一只腳沒有了。“這不是三羔嗎?”他見我在呼喚他,很不好意思地埋下頭。過了一會兒,他昂起頭,滿臉堆著苦笑,問我什么時候回來的?我一邊回答,一邊問他,“怎么成了這個樣子?”他說:“去年,腳被三輪碰了,走了幾家醫院,花了不少的錢,不知是醫生不精心還是自己沒操心,結果傷口化膿了,引起肌肉壞死,最終不得不鋸掉一只腳。”想他年紀輕輕、好端端的一個壯實后生,竟然成了一個殘廢,這后半生如何度過?我的心一陣陣痛楚……
時光如梭,歲月無情。唉,我那親愛的、可憐的鄉親們喲!
2007年5月27日晚草草于延安東關家中;
6月4日上午改定于延安東關家中
陜 北 的 山
陜北真是一個神奇而美妙的地方。說它神奇而美妙,并不只是因為它的地下埋藏了多少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富集的礦產資源;也不只是因為它的地上盛產了多少瓜果梨棗、五谷雜糧等綠色食品;更不只是因為生于斯長于斯的那些純樸善良的山民們和世世代代涌現出的英雄人物。而更多的則是因為它的山——神奇而美妙的陜北的山!
我常常懷疑造物主將世界上所有的山都堆在了這地球的一隅,使陜北成了山的世界,山的海洋!抬頭是山,低頭也是山;吃的是山,住的還是山;出門是山,回來仍是山。山是生存在這片廣袤大地上的人們的物質和精神寄托,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
我生在陜北,長在陜北,曾經和陜北的山零距離地親吻過。在這茫茫的大山深處,我扶過犁,拿過糞;吞過糠,咽過菜;淌過汗,流過淚。一切都是那么無助,那么渺茫。我對生我養我的陜北的山,鄙視過,厭倦過,一度時期,竟然埋怨起我的祖先為什么不把自己定居在廣闊的平原上、浩瀚的大海邊、秀麗的江南間,而偏偏要將家安在這貧瘠苦焦偏遠落后的千山萬壑中?使得日后的子孫們在這里永遠地受苦受難,千回百轉走不出大山,享受不到山外精彩世界的生活!我甚至怨恨大山,詛咒大山,盼望有一天天崩地裂,將這茫茫大山夷為平地;或者乞求上蒼有朝一日將這些綿綿山巒搬到天的盡頭,使這里的人們再也不要受苦受難了。但是現在想來,我那時是多么地無知,多么地任性,多么地忘本!如果當初沒有汲取大山的營養,沒有經過大山的磨礪,沒有遵循大山的教誨,我不可能體格健壯、意志頑強;更不可能走出大山、走向社會,譜寫人生美好的篇章!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要感恩大山,歌唱大山,回報大山!
陜北的山是雄壯的。當你登上高高的山巔,舉目四望,視野所及,蒼蒼茫茫,一望無際。山連著天,天接著山,天地合一,云霧飄渺。無數座山巒在陽光的沐浴下,恰似剛出鍋的一大籠熱氣騰騰的饅頭,正在等待著人們食用;那數不清的梁峁,千姿百態,形狀各異,像條條巨蟒、像只只雄獅、像頭頭大象、像個個巨人……盤踞在這廣袤的黃土高原上,正蓄勢待發;那層巒疊嶂的山脈,仿佛是大海的波濤,一浪接著一浪,涌涌不退,大有排山倒海之勢。總之,任憑你怎么想象,想象什么就是什么。
陜北的山是博大的。它胸襟開闊,無私無畏,可以容納世界的一切,包容人間萬象。如果你走錯了路,做錯了事,大山并不記恨你、拋棄你,依然像慈祥的母親一樣,緊緊地把你攬在懷里,教育你、鼓勵你、引領你重新振作精神,在人生的道路上繼續前進。我常常登上高高的山崗,仔細地俯視和尋覓著我那熟悉的村莊和親愛的同伴們。可是,任憑瞅花了眼,卻怎么也辨別不清,尋找不到!原來許多村莊隱沒在大山的皺褶里,而貌似高大的同伴們卻變成了一只只瘦小的螞蟻,早已不知去向。夜晚,睡在大山里就像睡在母親的懷抱一樣,是那樣的溫磬,那樣的甜蜜。有母親大山的呵護,有母親大山的擁抱,一切都是那樣的坦然,那樣的放心,那樣的無所畏懼。
陜北的山是純潔的。如果你坐在高高的山巔,細細地觀察,認真地品味,這廣袤的高原就像一泓清澈的湖水,綠意盎然,一塵不染。沒有喧鬧,沒有嘈雜,一片寂靜,遠處偶爾傳來幾聲雞鳴、狗吠、鳥叫、機器聲,升騰起幾縷裊裊炊煙,使空曠寂靜的大山顯得更加靜寂。如果你走累了,煩惱了,不妨走進大山,走上這高高的山梁,在那兒坐一坐,歇一歇,躺一躺,吸一吸清新的空氣,接受一下山風的撫摸,你的精神會頓時為之一振,心靈得到了凈化,一切疲倦和煩惱早已拋到九霄云外,驀然有一種返樸歸真的感覺。
陜北的山是神秘的。毫不夸張地說,迄今為止,人們對陜北的山的認識和探究仍然是浮淺的、表象的。關于它的物質,關于它的內涵,關于它的靈氣,仍需要一代又一代有修養、有品味的人們去探究、去挖掘、去解密。它像一個永遠解不開的秘密,像一部永遠讀不完的史書,耐人尋味,意寓深長。
我忽然明白了,陜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為什么走出了像李白成、高英祥、劉志丹、謝子長、李子洲等這樣的無數英雄豪杰和革命志士;為什么產生了那么多悲歡離合的動人故事和百唱不厭的像《蘭花花》、像《三十里鋪》、像《走西口》、像《東方紅》等信天游歌曲;為什么毛澤東主席將長征的落腳點、抗日戰爭的出發點、解放戰爭的總后方選在了陜北,而且在這里一住就是13年;為什么陜北人是那樣的豪放,那樣的仗義,那樣的純樸,那樣的勤勞,那樣的堅強?等等。我想這都是沾了陜北的山的靈氣的,是大山養育和熏陶的結果。
陜北的山喲,我怎能不謳歌您、向往您呢?
2009年2月28日下午草草于志丹寢室;
3月1日凌晨1時20分改定于志丹寢室;
同日晚23時50分再次改定于志丹寢室
我們曾經也年少過
祁玉江
人的一生最幸福、最愉快的當數童年和少年時代了。因為那個年齡段天真、爛漫、無邪,可以說無憂無慮,自由自在,腦海里除過想著吃飯外,就是玩耍了。那種甜蜜、快樂、有趣的生活,常常興奮得不能自已,以至有時晚上睡夢中都能笑出聲兒來。
我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小時候,雖然條件較差,生活艱苦,玩耍的形式和花樣遠不及城里的孩子。但農村有農村的特色,農村有農村的樂趣,玩起來也是那樣地開心,那樣地熱鬧,那樣地忘乎所以!我敢說,有很多有趣的生活是城里孩子們享受不到的。
每年驚蟄過后,首先必定會刮起老黃風。站在高山巔向北眺望,西北角上驀然騰起一股黃色的浪潮,越過座座山巒,排山倒海,向南涌來。頓時,天昏地暗,仿佛世界變了模樣。這時,鳥雀驚恐萬狀,在半空中奮力拍打著翅膀,幾乎失去了平衡,沒命似的四處逃竄;樹枝草木哆嗦著身子,發出嗚嗚的鳴叫,任憑狂風擺布;雞毛、雜草、紙片早已被刮得滿天飛揚,總之,能被卷起的東西,全被吹上了天,在昏暗的天空中旋蕩;行人搖搖晃晃,舉步維艱,瞇合著眼,抖動著衣服,躬著背,努力地向前爭扎著,嘴里還不停地謾罵著“這鬼天氣”。而我們這些幼稚的孩子們呢,則高興極了,一會兒張開雙臂,迎著狂風,肆意奔跑著,企盼被狂風一下子卷起來,像鳥兒一樣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一會兒跳上跳下,滿世界追攆著被狂風卷起的那些飄浮物,眼睜睜地盯著它們在半空中四處飄蕩,直至望不見為止;一會兒又拿起用高梁頸桿和紅紙做成的“風葫蘆”,在院子里、山路上快速奔跑,比賽著看誰的“風葫蘆”轉得快,痛痛快快地玩個夠。大風過后不幾天,便會聽到大雁的鳴叫聲。抬頭望去,幾十只大雁在天空中一會兒排成“人”字,一會兒排成“一”字,由南向北飛來。我們這些碎腦娃娃們早已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立刻跑上山崗,大聲地呼喊著“大雁大雁擺路路,黃米撈飯狗肉肉”和“亂了!亂了!”之類的話語。大雁聽到我們的呼喊,一時真的亂了方寸,立刻打破了隊形,沒命似的向北逃竄,直至遠離了我們才漸漸恢復了隊形。接下來便到清明了。漫山二洼,桃花開了,杏花開了,梨花也開了,粉的、紅的、白的,爭相斗艷,構成了一幅天然的“山花爛漫”圖。河灣里,柳枝吐綠;山坡上,草木發青,羊子已開始“跑青”。我們便和放羊人上山下洼,尋“索牛牛”、摘“馬奶奶”,要不就幫助大人們往回抱剛生下的羊羔。這時,燕子也飛回來了,在房前屋后繞來繞去,開始在屋檐下或窯洞里筑起了巢。一貫喜歡鳥雀的我們便關了門窗,滿屋里逮起了燕子,往往遭到大人們的一陣謾罵。“清明時節雨紛紛。”這個季節最容易下起濛濛細雨,天空灰蒙蒙的一片,空氣濕漉漉的,四周的山巒被籠罩在輕紗般的霧靄中。我們赤著腳踩在被小雨灑過的黃土小路上,軟酥酥的,好不愜意!回頭一望,身后便留下一行清晰的腳印。最使人興奮的是,每逢“清明”,母親和姐姐們便給我們捏起了“花花”,那用麥面捏成的諸如老虎、獅子、鳥雀、壯地蟲等各種動物,再點上紅點、綠點,活靈活現,煞是好看。我們一個也舍不得吃,就用細線繩串了起來,掛在窯幫上,白天晚上照著,生怕別人偷吃了。過了清明,便到了農忙季節,我們又和大人們一起下溝上山,種瓜種豆,灑下的是汗水,播下的是希望。
初夏,日子漸漸地長了起來,天氣愈來愈暖,大地的基色由黃變綠。白天,裊裊炊煙繚繞在村莊上空。我們與大人們在山里犁地累了,便連牛帶人躺在山坡上,以天作被,以地為床,頭底下枕著兩只破鞋,拉起了鼾聲,睡得昏天暗地,睡得自然香甜,怎么也爬不起來。猛地醒來,看到村子上空飄蕩著裊裊炊煙,是那么喜悅,那么迫切,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家中,端起飯碗美美地吃上一頓。夜晚,青蛙、知了不知從哪里竄了出來,滿溝里、滿樹上鳴叫著,此起彼伏,相互呼應,仿佛一首首悅耳動聽的交響曲,伴隨著我們進入甜美的夢想。進入盛夏,日頭格外的毒,天氣格外的熱,中午吃過飯,大人們常常為了乘涼,在鹼畔上的樹蔭下拉起鼾聲,呼呼入睡。可我們怎么也睡不著,不是甩著衣衫上山下洼追趕鳥雀,就是去溝灣里耍水嬉戲,要整整折騰上一中午才善罷甘休。有時把熟睡中的大人們驚醒了,難免又遭到一陣數落。于是,便輕輕地踩著碎步,躡手躡腳地溜走了。夏天的夜晚,天空寧靜而深邃,星星繁密而明亮,大人們在院子里或支了門板,或撂了席子,早早入睡了。可我們卻怎么也睡不著,好奇地仰望著天上的星星,感到無限的好奇,不停地數著,一遍、兩遍,久久不愿睡去。上小學的時候,我們幾個調皮的孩子不好好學習,常常愛逃學,往往早晨上學走在半路上,幾個人一合計,立即就不上學去了,便瞞著老師和家長調頭往回走,拐向麥地里逮山雞、追兔子。可逮了、追了大半天,最終還是兩手空空。這時,肚子早已餓了,但就是不敢回家,只好硬著頭皮,忍著饑餓,直等到天快黑時才偷偷摸摸地回到家中。事后家長的打罵和老師的懲罰就自然不必說了。
秋天到了,田野里的莊稼漸漸變得成熟起來。看到地里那些明胖胖的西瓜、綠茵茵的蘿卜、黃橙橙的梨子、紅彤彤的蘋果,嘴上早已流起了口水。一看四周沒人,瞬間便溜到田里,或抱了西瓜,或拔了蘿卜,或摘了梨子。離開時,還要倒退著拿柴草抹了腳印,生怕主人看出破綻,而后才立即逃在僻靜處,幸災樂禍地品償起來,自然又是飽餐一頓;有時來不及抹去腳印,被主人看出了端倪,人家便會順著腳印攆來家中,那種驚恐和尷尬的場面,至今想起來都是那樣地窘迫。進入深秋,大地開始下霜,玉米、豆子逐漸成熟,我們便偷偷地掰了玉米、拔了豆子、刨了洋芋,來到沒人處,架起一堆柴火,燒烤起來,還等不到燒熟,就津津有味地吃起來了。有時竟然被串起的火苗燎了眉毛,燒了頭發,滿嘴、滿臉被涂抹得烏七八糟,仿佛掏炭人一般,便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互相哈哈地取笑。終于到了收獲的季節,大人們在山里沒命似地收割莊稼,我們就提了小籃在收割過的田里撿拾起被遺棄了的谷穗、糜穗、豆子和洋芋來,往往滿載而歸,總算被大人們夸獎了一番。莊稼收割完,隨后便背到場上開始輾打。天快黑時開始分糧,我們便拿上口袋,提了筐子,與大人們一起將分下的糧食運了回來。看到滿囤里都是糧食,一家人臉上便揚起了幸福的笑容。
冬天是農家最清閑的季節,除了修梯田、積肥外,剩下的時間都在忙著自家的農活。有時也會自樂一番,幾個人便會湊在一起,“夢和”、“掀棋”。我們小孩子不會,便坐在大人們旁邊,仰著脖子觀看。要不,滿村里的男女孩子們聚集在一起,扇元寶、踢毽子、打碗碗、滾鐵環、滑冰車、捉迷藏,玩得遲遲不想回家,有時竟忘了吃飯。要過年了,我們掰著指頭一天一天算著,急切地盼望著過年的那一天的到來。離過年還有10余天甚至20余天,就開始置辦起年貨來,買炮竹、購香煙、稱洋糖。一片一百響的小鞭炮、幾個“牛腿”大炮、幾盒“羊群”和“晨鶴”牌香煙,便感到是最豐厚的家當,藏來藏去,生怕被別人偷走似的,一個都舍不得放,一支都舍不得抽,直要等到過年那天晚上才拿出來慢慢地享受……
農家自有農家福,農家自有農家樂,農村的孩子自然也有農村孩子的歡樂和幸福。現在,我們已年過5旬,再也享受不到孩提時的那種生活,找不回當年那種歡樂和幸福。可是,當我們看到城鄉孩子們茁壯成長的情景,一種無比幸福美好的感覺便會油然而生。我們多么希望孩子們快樂地學習,快樂地生活,快樂地成長,盡快成為祖國的棟梁之材,為自己的人生書寫更加燦爛的篇章。因為,我們也曾經年少過。
附:評介文章
重建倫理的故鄉
李敬澤
祁玉江在寫作中成為一個回憶者。
回憶之“回”是回到往昔,回溯逝去的時光。但對祁玉江來說,回憶也是回鄉,回到他的陜北高原上的故鄉。
——那里有他的沉默如山的父親、明達慈祥的母親,他的哥、姐,他的鄉親,他的恩師;有兒時的明月、草木,有大地上無休無止的勞作,還有民歌、秧歌、轉九曲、高亢的嗩吶和夢一般的鄉村電影……
埃德蒙·威爾遜在論述普魯斯特時寫道:
“普魯斯特可能是最后一位研究資本主義文化的歷史學家,其作品中的愛情、社會、知性、外交、文學和藝術皆令人心碎。而這位有著憂愁而動人的聲線、哲學家的頭腦、薩拉森人的鉤鼻、不合身的禮服,和仿似蒼蠅復眼一樣看透一切的大眼晴的細小男子,主導著場景,扮演著大宅里最后的主人的角色。”(《阿克瑟爾的城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
祁玉江和普魯斯特,就好比黃土高原和巴黎,其實比不得。我之所以想起這段話,是因為回憶構造一個世界,在這世界里,回憶者是主人。祁玉江,我沒有見過他,但他的臉上必是有風霜的,他身上依然懷著與生俱來的“苦水”,他的筆調親切感慨,他的回憶樸素翔實,只是為了確證一件事——
吾土吾民。這是我的土地,是我所歸屬的人民。
回鄉之路,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所建構的新主題。古人的回鄉是真回鄉,狐死首邱,葉落歸根,故鄉在中國古人的世界觀中是一切意義的中心和歸宿,游子心中永遠攜帶著故鄉,它從來不會成為精神上的重大疑難。但在現代,難局出現,遂不可解,《朝花夕拾》里,所有溫暖的、憂郁的回憶終究是證明:回不去了,不回去了。這是中國精神的根本決斷,這種決斷也標志著生命中的“斷”;生命的意義與故鄉、與兒時的生活世界無關,那意義在遠離故鄉的地方,在山外山、天外天。
所以,現代以來的文人特別愛回憶故鄉,“逆子”自贖,生命中的斷口要以記憶修補。直到現在,直到這個世紀之初的“新散文”中,他們還在詠唱著——這種詠唱是有效的,在詠唱中,故鄉不再是意義的中心而成為審美的對象,書寫著“主導著場景”,扮演著“最后的主人”,似乎故鄉已成廢墟,荒無人煙,而他是一個可憐的敏感的人,一個不幸失去他的世界的人——本質上是“客人”。
——這當然是精致的謊話。但這種謊話在世紀初文學散文中反復書寫,越寫越像真的了。
所以,讀祁玉江這些文章,一個意外的結果是,讓人看出了通行的故鄉回憶的虛矯。
祁玉江從未掩飾他是多么渴望離開故鄉,他對自己成長經歷的回憶有一種動人的樸素;那是祁玉江一個人的路,但也是中國人的路。在悠長的歲月里,在中國的鄉間,無數天資聰穎、懷著夢想的孩子們,都知道讀書意味著什么,“金榜題名”意味著什么,那是清苦生活中的希望,是人間的喜慶,是一個人離開“家”,走向“國”、走向“天下”。
“家國天下”,古圣先賢就是這么教導中國人的,在古老鄉間,父親和母親、那些嚴厲的懷著大責任的教師們也是這么教育孩子的,在祁玉江成長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父母和教師們已經不會從古老經典中引證什么,但失其辭而存其意,他們對這孩子的教育其實還是不曾割裂家國天下,那是一套貫通的倫理:一個人對“家”的責任就是對“國”、對“天下”的責任,在這個世界圖景中,認同未曾割裂,人無論走多遠,無論世事如何變遷,他不會失去他的故鄉。
由此,我們能夠看出故鄉對祁玉江的意義——
當然,那是美的,但祁玉江從來不曾把它當作審美對象——他不曾以新獲得的眼光觀賞它,當然,他也不曾以新獲得的理念去批判它,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他是這個世界的主人——這主人其實是個復數,“我”之中就有“我們”,他寫道:
“我二十歲以前曾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與我親愛的鄉親們一起下過地,扶過犁,拿過糞,受過苦。感謝上蒼,二十歲那年只因參加了一次‘無所謂’的高考,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從此離開了大山,離開了我那日夜廝守的鄉親們。我常常想,我之所以能從大山深處崎嶇的山路上走出來,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是沾了大山的靈氣的。如果沒有經過大山那段艱苦生活的磨礪,沒有親愛的鄉親們的幫助和呵護,也許我現在仍然和他們一樣。從這個意義上,我有責任歌唱大山,改造大山,拯救大山深處我那親愛的鄉親們!”(《只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的深沉》)
細讀這段話,這里沒有任何斷口:一個人從大山走出去,但生命不曾由此斷裂,在祁玉江看來,故鄉的一切,雷霆雨露,皆是恩情,對故鄉的認同深深地生長在他的自我意識之中。
祁玉江的故鄉是倫理的故鄉,故鄉所證明的是一個古老倫理的世界——一種儒者安身立命的世界觀。這種倫理樸素、直觀,推已及人,父母鄉梓之恩便是天下百姓之恩,對天下盡忠便是對家鄉盡義。祁玉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責任”,他說:“我有責任……”,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有了這份內心承擔的責任,故鄉才真的是故鄉。
所以,祁玉江的這些文章是“親”的。很多人寫故鄉,文章不可謂不好,但實在太像文章了,反而不親,把故鄉當了他鄉。祁玉江的回憶片斷、隨興,他不是要寫文章,他只是情動于中,有話要說。他于萬物萬事皆是有情,這份情也是尋常人情——他是游子還鄉,坐下了就能閑話桑麻,似乎歲月不曾流逝,似乎一個人不曾離開故鄉。
——這是中國精神中最珍貴的一脈,古老鄉村之生生不息靠的就是它的精英們的這點根本之思。這一脈五四之后斷了,游子們去不回頭,任鄉村在他們的身后破敗。
在這個意義上,如何看待“故鄉”,非關文章,其實是中國現代性演化過程中的基本疑難,如果故鄉不是倫理的故鄉,如果在我們的文化中沒有對鄉村大地的深刻認同,那么,新農村建設恐怕終究不過是修路蓋房子而已,修路蓋房子很重要,但鄉村能否成為人的安居之地,關乎路、關乎房子,更關乎人心。
祁主江是回憶者,也是實踐者。他白天行動,晚上回憶他的故鄉他的老家。與故鄉同在者有根,根在家國天下,有根者必選擇先憂后樂。
是為序。
樸素是一種大美
——序祁玉江散文集《山路彎彎》
高建群
這是一本樸素的書。在這本名曰《山路彎彎》的書里,一切都是以一種樸素的形態存在著的。樸素的事物,樸素的感情,樸素的文筆——透過這些,我們看到了作者一顆樸素而真誠的心。
“樸素是一種大美”,這是幾年前散文家周濤先生告訴我的。那次,他從山西老家回來,路經西安時,給我談起山西作家,說趙樹理是中國最樸素的小說家。如今,在閱讀《山路彎彎》的時候,我想起周濤的話,想起“樸素”這兩個字。
本書作者玉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們大約有二十年的交情。那時,我在延安報社當副刊編輯,有幸為他編發過《金色的月亮》。記得,這是從一大堆稿子中篩選出來的。每天,傳達室都要拿來一大堆來稿,堆在我的桌子上。用稿率是非常小的,每天大約選出一篇備用。那天,《金色的月亮》從一大堆稿中跳了出來,記得,我當時是多么地欣喜呀!那個年代的編輯就是這樣。
是文章中那種饑餓、無助感動了我。我像看到了小時候的自己。而文章的構思又極為精妙:小時候,饑餓的我望著山背后的金黃色的月亮,將它想象成一個大餅;許多年后,當我重返家鄉的時候,為了當年的緣故,母親專意烙了一張黃金大餅給我吃。
如果說,當年的《金色的月亮》,讓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人生片斷,那么,如今捧讀這本叫《山路彎彎》的書時,我就能夠從容地、全面地、心貼心地看到一個從大山中走出的農家孩子的心路歷程了。
我十分喜歡像《長相思》,像《山路彎彎》,像《金色的月亮》,像《走南路》,像描寫父親、母親的那些篇章。作者口無遮攔,徐徐道出,是如此的樸素又是如此的真誠。一個吸吮著苦難乳汁成長起來的山里孩子的形象,躍然紙上。
我不久前去了一趟作者的家鄉。“三岔”位于陜北高原腹心地帶,那涌涌不退的大山,一座座相擠,一座座相連。作者的家鄉就在子長、子洲、橫山交界處的一座山崗上。山路彎彎,走在這樣的山路上,你會有一種“一山放過一山攔”的感覺。
確實,三岔地區的蠻荒,僻遠,山大溝深,生存條件的不易,較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寫的安塞、志丹的情況,還有過之。斯諾當年曾望著這涌涌不退的大山,把它比做印象派繪畫,斯諾說:“人類能在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生存,簡直是一種奇跡!”同樣地,三岔地區較之路遙《人生》中高加林形象所生活的背景延川,亦更為過之。
站在山上,我真不能想象,玉江老弟是怎樣一步一步從這大山里走出來,走進城里,走到今天的。一代一代的三岔人又是怎樣從這大山里走出來的。而又有多少人,倒斃在這彎彎的山路上,永遠沒有走出,永遠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樣子。更有多少人,還廝守在那里,繼續著他們的生存,做著家園的最后守護者。
苦難的陜北大地呀!
英雄莫問出處!這是時下的一種流行時尚。就連我自己,有時候在有些場合,也不能免俗。玉江先生已經是一名領導干部了,但是我們看到,在這本叫《山路彎彎》的書里,他多么的真誠呀!他無遮無攔地將一個透明的自己端給讀者,他為他曾經是大山的兒子而驕傲。是令我尊敬的地方!這樣實在的人他是能干成大事的!
這樣坦誠的陜北人我還遇到過幾位,例如艾丕善先生。1983年秋天,在子長縣招待所吃飯,當所長問艾書記對伙食有什么意見時,艾丕善慨然說:“我一個討吃的出身,今天能吃上這么好的一桌飯,我哪還敢有半句彈嫌的!”當時,旁邊的我因為這句話而對艾先生肅然起敬!
在《山路彎彎》付梓的時候,我寫上以上的話。
我在許多年前說過,造物主還是公平的,陜北人太苦難了,所以作為補償,它打發來許多夢想家,讓人們用夢想來填補無奈和稀釋苦難。在閱讀《山路彎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的尊貴的朋友祁玉江先生,亦是這樣的夢想家之一。
重回故鄉之路
——祁玉江散文集《我的陜北》閱讀札記
谷禾
1、我沒有問過祁玉江《我的陜北》的涵蓋,但我相信,它是祁玉江迄今最重要的一本散文選集。說它重要,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從中體驗到了一顆赤子之心的鮮活跳動,而且寫作者祁玉江也通過《我的陜北》尋找并且重新回到了他的精神故鄉陜北高原。
在我的閱讀視野里,無論是20歲即漂泊歐洲大陸的作家詹姆斯·喬伊斯,還是大半生生在全美各地浪蕩的威廉·福克納,代表他們最杰出文學成就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生養他們都柏林城和郵票大小的約克納帕納塔縣。我想這絕不會是上個世紀兩位最偉大小說家的巧合。我是說,這個世界沒有誰是天才,即使如喬伊斯和福克納這樣的文學巨匠,其所知和能知依然是有限的。所以對于作家而言,最重要也最艱難的是如何用沿著語言和記憶鋪成的道路,尋找并最終回到自己精神的故鄉。
作為中國文學母題之一,“故鄉”一直被無數代作家反復抒寫,葉落歸根也罷,歸心似箭也罷,狐死首丘也罷,無不是因為精神的無所依傍,幾乎讓肉體也無法支撐了,所以人們要翻來覆去地追尋和追索。其實如果所有的生都源于死,人類從離開母體那一天起,就再也回不去故鄉了。人類活在這個世界,注定是要承擔風或“人生無處不青山”地偶爾釋懷一下。
在《我的陜北》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年來一直走在回故鄉之路上的鄉村赤子祁玉江——他的年齡在歲月的風霜中無情地增長著,他記憶的精神故鄉卻異常清晰真實起來——他沉默的父親、仁慈的母親,他的用生命扛起苦難的兄弟姐妹,他隱忍的師友和鄉親,他的櫛風沐雨的老屋,他的扎根黃土的草木,他的疼痛、困惑、煩擾和熱愛。我想,這是《我的陜北》的魅力之所在,更是祁玉江的人格力量之顯現。
2. 關于散文的尺度,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叫“心性”的詞兒。我想,能以自己的“心性”把真實地“情懷”想清楚、”干干凈凈地“表達清楚”,自然就該算不差的散文了。
祁玉江的散文不矯情,不造作,樸實無華,真情流露,字里行間充滿著對生活的摯愛,對理想的追求,一如其人。譬如,他寫自己沒有滿足父親小小心愿的悔恨:“聽著母親的訴說,望著躺在靈柩里的父親慈祥、清瘦的臉頰,那一刻,我心如刀絞,扶住他老人家的靈柩失聲痛哭……我不斷地詛咒自己:我自私,我是一個不孝之子,80歲的老人提出這樣一個小小的愿望(去延安看看火車),我竟然都不能滿足,我算是什么兒子?”又如他寫少時讀書跑灶(走讀)的辛苦:“晨風嗖嗖,繁星點點,四周黑幽幽的一片靜寂,遠處不時傳來貓頭鷹和狐貍的怪叫,使人毛骨悚然,不敢前行。這時,母親便提了燈籠,踮著小腳,把我一直送上山巔。”他寫回鄉的煩擾:“回到家中,一下車,圍上來不少人。除了我的家人還有一些親戚以及幾十里路外趕來的群眾,一個個要求我給他們辦事:有學生分配的,有求提拔的,還有包攬工程的,游說干部調動的……一個說完又一個,吵得我頭暈腦脹,心煩意亂。只好吩咐隨從趕快收拾東西,匆匆返回。” 這樣的描寫不刻意拔高,不肆意渲染,不回避內心的矛盾和困惑,最大限度的用樸實、真情、摯愛的文字還原生命最真切感受,反而具有了撼動人心的力量。連他的情感也是沒有絲毫虛飾的。他在回憶中感動,感慨,感傷;他在咀嚼中反思,反問,反省。他所經歷的苦難積淀成了他人生寶貴的財富,并因為對精神故鄉的熱愛而化成了內心源源涌流的甘泉。
3. 祁玉江對自己的精神故鄉懷揣著巨大的敬畏和感恩之心,他借用艾青的詩句這樣表達:“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眼淚?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祁玉江在后記里寫道:“我之所以能從大山深處崎嶇的山路上走出來,走到今天這一步,是沾了大山的靈氣的。”而在《我的陜北》里,除了生養他的那一片厚土,祁玉江懷著最深厚感情就是逝去的父親和年邁蒼蒼的母親。
多年以前看過一部叫《天堂電影院》的意大利電影。在電影里,迷戀電影的小托托當上了天堂電影院的放映員,想要放棄上學時,老放映員阿爾夫萊多語重心長地告訴他:“不,別這樣,不上學你將來會后悔的。這并不是你真正的工作,現在天堂需要你,你也需要天堂,但這只是暫時的。有一天,你會去做其他事情,更重要的事情。相信我,世界上還有許多比這更重要的,重要得多的大事。”當青年薩爾瓦多(托托)從部隊回到故鄉,感到茫然與失落時,阿爾夫萊多又指點他:“生活和電影中不同,現實要艱難得多。離開這兒吧,回羅馬去,你還年輕,世界是屬于你的。” 阿爾夫萊多把他用一生換來的經驗教給了薩爾瓦多,年輕而不知世事的薩爾瓦多于是超越了阿爾夫萊多,一步步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可以說,沒有這個守候在故鄉的阿爾夫萊多,就沒有日后著名的著名導演薩爾瓦多。是老一代人“不變”的主題,催生了新一代人“變”的主題。
從這個角度說,祁玉江的父親母親又何嘗不是他的阿爾夫萊多呢!
4.作為一個詩人,我用自己一首詩的片斷來作為這篇閱讀札記的結尾:“那本來可能發生和已經發生的/指向一個終結,終結永遠是現在/足音在回憶中回響/沿著我們不曾走過的那條通道/通往我們不曾打開的那扇門……”
 冬天的留影
冬天的留影
相關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
網友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