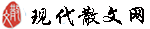評(píng)論家針砭當(dāng)下散文
當(dāng)下散文創(chuàng)作最近引起評(píng)論家更多的關(guān)注。評(píng)論家們?cè)诳隙ㄉ⑽膭?chuàng)作成就的同時(shí),也尖銳地批評(píng)了其中所存在的問(wèn)題。
王兆勝在《南方文壇》第4期撰文說(shuō),自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guó)散文確實(shí)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輝煌,但同時(shí)也埋下了危險(xiǎn)的隱患,而這種危險(xiǎn)被散文界不斷擴(kuò)大而不自知。今天的散文已在歧途上越走越遠(yuǎn),要獲得更大的發(fā)展,它必須進(jìn)行新的調(diào)整,不論在觀念還是在實(shí)踐上都應(yīng)該如此。無(wú)度與失衡是當(dāng)下中國(guó)散文存在的第一大困境。自從散文變得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甚至于愛(ài)怎么寫就怎么寫,尤其是余秋雨將散文當(dāng)做可以縱橫馳騁的疆域進(jìn)行創(chuàng)作實(shí)踐并大獲成功后,散文的面目就與以前大為不同。從優(yōu)點(diǎn)方面說(shuō),它使散文變得更自由了,而且獲得了巨大潛力、活力和中心地位;但其缺點(diǎn)是背離了散文的常識(shí)和本性,進(jìn)入令人吃驚的“失范”狀態(tài)。最突出的“失范”是文章以“長(zhǎng)”取勝,動(dòng)輒萬(wàn)言甚至數(shù)萬(wàn)或十余萬(wàn)言,人們對(duì)“大”散文的理解過(guò)于看重文章之“長(zhǎng)”。一些作家的散文確實(shí)改變了以前的“小格局”,但不加節(jié)制的散漫卻是共同的。另外是欲望的放縱,這包括寫作欲、發(fā)表欲、表達(dá)欲。我們不妨對(duì)散文家的創(chuàng)作量進(jìn)行研究,有的高產(chǎn)到了比復(fù)印慢不了多少;有的一稿多發(fā),竟達(dá)數(shù)十次之多;還有的隨意抒發(fā)感情,給人空洞不實(shí)之感。任何事物都有一個(gè)“度”,超過(guò)了度也就“物極必反”。散文亦然,沒(méi)有限制而過(guò)于隨意地書寫,必然使之變得支離破碎、不可收拾。因此,當(dāng)務(wù)之急不是讓散文之“形”繼續(xù)“散”下去,而是聚合起來(lái)。當(dāng)下中國(guó)散文的第二大困境是“神”散或無(wú)神。當(dāng)前的許多散文分成若干甚至幾十個(gè)段落,還有的用互不相干的小題目聯(lián)綴成篇,成一集錦體,這一面帶來(lái)文章結(jié)構(gòu)的松散,更重要的是主題分散、精神離散和靈魂出竅。翻開今天的散文雜志,這種散漫氣泄之風(fēng)如疾病一樣流行,少有不被感染者。“腦”大于“心”,有的作品處于心靈“缺位”狀態(tài),這是當(dāng)下中國(guó)散文的第三大困境。如果從增強(qiáng)知識(shí)和思想含量的角度看,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的中國(guó)散文確實(shí)有了較大的改觀,這主要表現(xiàn)在密度、厚度和深度加強(qiáng)了;但從心靈和人生智慧的角度觀之,它又明顯表現(xiàn)出淡化和萎縮之勢(shì)。于是理智大于情感、頭腦大于心靈、思想大于智慧成為相當(dāng)普遍的現(xiàn)象。散文是最重心靈散淡自由的一種文體,如果過(guò)于用“腦”推理,散文之心就容易變得焦躁、生硬、不平,甚至縮小枯萎。何況有的說(shuō)理并無(wú)見(jiàn)解,而是味同嚼蠟。
王兆勝認(rèn)為,散文正面臨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以來(lái)最為嚴(yán)峻的時(shí)刻,20年的探索與解構(gòu)已使它走進(jìn)了死胡同,傳統(tǒng)的資源早已被棄如敝屣,新的觀念尚未形成,這就是時(shí)下中國(guó)散文的“窮途末路”。
張宗剛在《文學(xué)自由談》第4期撰文說(shuō),當(dāng)下散文隊(duì)伍空前壯大,散文創(chuàng)作數(shù)量激增,但真正關(guān)心社會(huì)問(wèn)題、展示心靈本相、富于社會(huì)責(zé)任感和道義感的文本卻不多見(jiàn)。他尤其尖銳地指出,公款旅游游記散文漸漸淪落為公款玩樂(lè)的遮羞布。只要稍加留意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在當(dāng)下車載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記散文里,都有著官本位意識(shí)的坦然流露。這類文本呈現(xiàn)給我們的,往往離不開公款消費(fèi)的背景,離不開與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種種公款接待的規(guī)格規(guī)模、檔次排場(chǎng)。許多明顯帶有“官員”標(biāo)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不是“參觀”,就是“出訪”;不是“采風(fēng)”,就是“視察”;不是這個(gè)當(dāng)陪同,就是那個(gè)做跟班。如此畫蛇添足般的語(yǔ)言在某些作者那里竟成了必不可少的文字鋪墊,成了身份高貴的必要詮釋,卻不知它們是與文學(xué)和審美、與詩(shī)意和境界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散文之?dāng)场T谏⑽闹谐霈F(xiàn)該類文字,正如同在古裝影視劇中出現(xiàn)電線桿、摩托車、手表等“穿幫”鏡頭一樣不倫不類。稍有判斷力的讀者,讀到這樣的文字都絕不會(huì)產(chǎn)生愉悅感。出于顯示身價(jià)、標(biāo)榜自我的需要,一些作家的文字沉迷于種種迎來(lái)送往、前呼后擁、推杯換盞的場(chǎng)景描述。如此三句話不離官本位的游記散文,實(shí)際上就是享受腐敗和記錄腐敗的散文。當(dāng)現(xiàn)代人的旅游多已變成為一種走馬觀花式的眼球經(jīng)濟(jì)時(shí),也便宣告著李白、徐霞客那樣在寄情山水嘯傲煙霞的萬(wàn)里獨(dú)行中生成的那種與風(fēng)物合一、與自然同娛的闊大情懷的失落。當(dāng)公款旅游成了以傳播真善美為主旨的散文中的美妙談資時(shí),也便意味著散文的道德底線與審美底線的消失,其所帶給讀者的閱讀感受,除了可笑可鄙,更多的是苦澀和沉重。
相關(guān)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
網(wǎng)友評(píng)論(共有 0 條評(píng)論) |
散文信息
| 著名作家財(cái)神 | 孫犁的意義 | 首屆“絲路散 | 陜西散文界新 | ||||
| 陜西6位作家獲 | 賈平凹:散文 | “孫犁文學(xué)獎(jiǎng) | 解晚晴美文集 | ||||
| 恕我直言--不 | 詩(shī)性美文中的 | 散文的尷尬 | 自然散文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