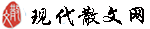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新散文時代”的異光
2010年4月對于漢語也許并不會留下縱切的刻痕,但就散文界而言,有幾樁出版事件麇集一時,卻足以構成一種意味深長的表達。在成都舉行的第20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期間,朱大可和張閎攜帶新著《眼與耳的盛宴》和《鐘擺,或卡夫卡》,以犀利的話語方式,展示了一種透視文化肌理的沉著和大氣。兩書是他們作品中最具思考意味的,無論文風還是行走的深度都要超過以往作品;散文家、詩人鐘鳴在白夜酒吧舉行了隨筆集《涂鴉手記》和《畜界·人界》(修訂本)的首發式,暗示了這位多年躬行于蜀地文化的行者,直腰而起的豐滿形象。與此同時,祝勇、周曉楓、龐培、蔣藍、趙荔紅等多位“新散文”代表作家與詩人柏樺、陳冬冬、林克等齊聚江蘇南通,圍繞祝勇的散文論著《散文叛徒》展開對話……這些信號似乎表明,漢語散文的發展,已經完成了由浮躁的宏大歷史敘事、囈語般的私人書寫到回歸散文本身的文學轉向,這就像一抹異光,在大地上用一種“涂鴉”的方式,記錄了散文的轉身。
“旱地渡船”與新散文
如果說當代漢語詩歌經歷了地下、民間、公開化的歷程,那么,“新散文”從一開始就是在民間尋找自己的“涂鴉”胎記。祝勇認為,如果“背叛”不是出于外在的壓力,那么它必將出于內在的抉擇。當我們已經無法從現有的文學表達體系中尋找到哪怕一絲快感,認同的危機就必然會發生。這時,迫使一些具有文學自覺的人將自己的寫作與那些被公認為主流的寫作等同起來,就是一件強人所難的事情。只有意識到這一點,真正的解放才能開始。對于散文寫作者而言,這樣的覺悟來得太晚。很多年后,我們才發現昔日的散文英雄無不成為搞笑大師。
把散文寫成生活流水賬,或者把散文弄成觀念意識的“火藥包裝紙”,這兩者都不屬于散文應該抵達之地。在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固然有混亂的表象,但更有價值的底線存在。很多人希望在這種文學體裁里注入太多的元素,那可以成為論文,成為批評,成為考據,成為檄文,或者成為關注底層生活的考察記錄,但這些不是嚴格意義的散文。一種人渴望推倒既往散文譜系而樹立自己的散文觀為圭臬,宣布不通過自己發明的“旱地渡船”并留下擺渡錢就無法抵達經典地帶。這讓我聯想起俄羅斯作家索洛烏欣在《掌上珠璣》里提到的一則掌故: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評價一個無才華的詩人時說:“他這個可憐的人,一生總是在旱地上拖著小船!”我們身邊大樹圭臬的人才華甚多,反而是那些入其彀中者,在旱地拼命拖著小船沖向“經典”地帶。還有一種人,棒殺制度之外的新散文言路,至今還在做大帽子的批發生意。這些行為,一者是“出名焦慮癥”的周期性發作;二者是顧忌話語權力的旁落。表面看來,他們似乎處于兩級對壘,但基本上操持的都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非文學策略。
鐘鳴認為,新散文的這一批散文家,在對生活輻照度、穿透力方面尚需開拓、審思,不必過于迷戀私人文體的威力,但他們基本就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散文寫作的高峰時刻。
2005年10月,蔣藍在“中國新散文批判研討會”上,陳述過如下觀點,“新散文”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新時期”以來明顯區別于楊朔式散文,開掘個人心路和生命體驗的散文的總稱;二是指以祝勇、周曉楓、鐘鳴、張銳鋒、于堅、寧肯、葦岸、馮秋子、翟永明、龐培、蔣藍、凸凹、王開林、格致等為主的、以《布老虎散文》為根據地、相對松散的新銳散文家。與《七月》詩人不同的是,目前尚未形成新散文清晰的流派概念,他們只是逐漸形成了有關新散文在思想、美學、文體意識方面的趨同。當然,新散文展示得較為充分的是在文體的“破與立”方面。2002年,新散文的領軍人物祝勇寫出了長篇論文《散文:無法回避的革命》,對“新散文”進行了階段性總結。著眼于文體,他列出了長度、虛構、審美、語感四項指標,論證了新散文所不同于制度散文的特質。散文的叛逆者們不可避免地對所謂制度散文表現出不信任,從而尋求一種更接近內在真實的表述方法。“這些探索者們更專注于自己的內心,因為專注內心比輕視別人更能顯示一個創造者的自信。”而在祝勇的論著《散文叛徒》里,他已經遠遠不再滿足于文體的叛逆了。個人化思想以及對現實的拷問,正在成為新散文的思想內核。
有關研究者指出,不是我們如何創造了新散文時代,而是這個新散文時代的氛圍如何支配了我們的寫作?這涉及到散文的時代意義問題。在為漢語散文文本祛魅的同時,人們必須注意,如果無視祝勇主編的數十期《布老虎散文》、數卷《閱讀》以及多本《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散文卷》秉承獨立、高揚自由、堅持創造的精神向度,歪曲他們在思想領域的價值取向,甚至以生活在底層/上層的經濟身份來質疑這批作家的社會處境和動機,不但游離了文學的前提,也無疑是對新散文的妖魔化。散文家們將嚴格意義的散文與思想隨筆,推衍到了一個更為開闊的新散文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凸顯出新散文之于漢語文學的現實意義。
新散文與大地的形態
在詩人、散文家蔣藍看來,大地的根性往往缺乏詩性,缺乏詩性所需要的飄搖、反轉、沖刺、異軍突起和歷險。也可以說,詩性是人們對大地的一種烏托邦設置;而撲出去而忘記收回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無心的天地造化,仔細留意,卻發現出于某種安排。一百多年前,黑格爾曾斷言:“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史詩,因為他們的觀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這是特指東方民族沒有史詩情結,卻道明了實質,讓思想、情感隨大地的顛簸而震蕩,該歸于大地的歸于大地,該賦予羽翅的賦予羽翅,飛起來的大地與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對而生,成就了當下的新散文。而鐘鳴的智性寫作,堪稱代表。
很顯然,一個沒有多少經歷的人,很難觸及經驗性寫作;而一個無法對經歷進行處理的人,其經驗性根本就無從談起。個體經驗不可能絕對化。閉門造車的天才就不在此空域內,他們高起高打,不可言狀。談及經驗寫作,讓我想起一些寫家老是要糾纏語言、語感、語義之類的問題。一個作家如果連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就好像隔著玻璃在研究魚和水的關系。目前,在這個只能依靠經驗性寫作才能發力的寫作領域,人們傾向于談論詩或散文,而不是語言或語感,隱喻或反諷。因而,在論述新散文過程中談論題材、語言、審美、閱讀史、生活史之類就沒有太大的必要。嚴格地說,比起過往的寫作人,我們的確難以再發現什么了,很多所謂的“洞見”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又閃爍在文學愛好者的低空。盡管它們均是經驗的構成部分,但還不是文學的經驗性。從個人化的生活史中彰顯既符合歷史語法、又迥異于宏大敘事的言說,我們可以通過祝勇等人言說的指向,抵達那看不見的所在,以“說出——照亮”的命名方式,正在成為一種檢驗寫作人實力的標尺。
祝勇指出:“紙上的叛亂終將發生,遲早有人要為此承擔惡名。但是,對于一個健全的文學機制而言,背叛應是常態而非變態,因為只有背叛能使散文的版圖呈現某種變化,而不至于像我家窗下的臭水溝一樣以不變應萬變,這是一個無比淺顯的道理。散文叛徒們與‘斷裂’主義者的區別顯而易見:后者的利刃斬斷過去,而前者的道路通向未來。”
相關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網友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