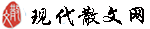詩與人是一次次的奇遇
詩與人是一次次的奇遇
沈葦
涉及到詩與人的話題,我們很容易往大的方面去思考,變成了諸如詩與讀者、詩與人民、詩與社會、詩與時代等關系的談論,有時,成了一個大而無當的話題。我并不是說,這樣的談論是多余的。只覺得,僅從社會層面和傳播意義的角度去談論詩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能不能將這個話題往小里談一談?能不能往一首詩生成的時刻那種詩與人的關系的角度去想一想?能不能將這個話題放在具體的詩與具體的人上?對于一個詩人來說,一首詩的誕生是一個重要而神圣的時刻,但我們往往忽略了它。
這個時代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詩歌現象,我們被現象困擾,錯把現象史當作了詩歌史。孰不知,詩人不是由現象來支撐、歸類的,而是由時間來甄別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更需要從大回到小,回到具體的詩與具體的人,從博爾赫斯所說的“人群幻覺”回到希門內斯的“廣大的少數人”。
當一個詩人坐下來寫作時,他絕對是一個本質的人,一個煥然一新的人,同時是一個忘卻了時間與焦慮、得到了詩歌庇護與救贖的人。這樣的瞬間,豐盈高過了貧乏。這個瞬間會持續,會穿越漫長的貧乏,與另一個豐盈的瞬間相遇。正是這種詩與人相遇的瞬間、詩與人的奇遇記,使我們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并精神振作、一躍而起。
詩與人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困惑、一個謎團,也是一種驚訝、一個奇跡。當一首好詩誕生時,詩人是吃驚的,這首呱呱墜地的詩對詩人也是吃驚的。如果非要拿詩歌寫作與小說寫作進行一番比較,我只想說,詩歌寫作中有更多的奇跡,更多的意外,更多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而小說寫作,更像是一場預謀,有時是一個“水龍頭”,只要打開,就會流淌。這正是二三流小說家藐視詩歌而一流小說家敬重詩歌的原因。一首詩誕生了,詩人為他漫長的一千零一夜找到了一縷曙光。每一首詩都是迎向曙光的一扇窗戶。
有一位西部的小說家曾勸我不要寫詩了,因為按照他的說法,寫詩是沒有出路的。在這里,我想引用泰戈爾《孟加拉風光》中的話來回答他的“好意”:“如果我能一天寫一首詩,我的生命將在一種喜樂中度過;雖然我侍弄詩歌已經有幾個年頭,但它還沒有被我馴服起來,還不是那種讓我隨時套上馬頭的飛馬。”
我們常常談到詩歌的出路問題,詩人們在談,文學界也在談(帶著一種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口吻)。我覺得沒什么好談的。這個問題是一種虛構,是不存在的。詩人們在寫作,這本身就是出路;詩人與詩在一起,這已經是出路。再說,有了出路又能怎樣?出路之后的路又在哪里?詩人們不是在尋找出路,因為詩已經在路上,當然是在一條困難的路上。
一個詩人過了四五十歲還在寫作,并且越寫越好,詩歌寫作在他已是一種個人修行,同時有了更大承擔。在今天,我們不要夸大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力,文學已經很邊緣,詩歌更是邊緣中的邊緣。然而,正是這種邊緣化了的“審美的孤獨”,保證了詩歌的純正性和毫不妥協性。詩歌永遠走在各種文學的最前面,它是文學中的“探險隊”。
詩與人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沉默。在一個喧囂的充滿了各種詩歌現象的時代,沉默往往是最有力的聲音。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要在沉默中微笑,并信任那些安靜而有耐心的詩人。
相關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網友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