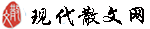想起了羅門,想起了昌耀
想起了羅門,想起了昌耀
——有關(guān)“詩歌與人”的話題及其他
風(fēng)馬
臺灣詩人羅門和青海詩人昌耀,這兩位是中國當(dāng)代詩歌的自由吟唱者,他們癡心于詩,特立獨行,在蕓蕓眾生中,以詩歌這種崇高的藝術(shù)形式證明了自己的存在。盡管一個頭戴荊冠,一個頭戴桂冠,一個是“大山的囚徒”,一個是海外游子;盡管他們的詩觀及人生觀不同、人生境遇和生活質(zhì)量也完全不一樣,但在我眼里,他們都屬于那種能夠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力奉獻給詩的人,是真正意義上的詩人,而不是那種不官不民附庸風(fēng)雅追風(fēng)趕月心猿意馬之流。雖然說中國詩壇早在上世紀(jì)80年代末就在經(jīng)濟大潮的沖擊下趨向沉寂了,現(xiàn)在又在全球化的娛樂文化、多元文化的全民消遣和多重選擇中“風(fēng)光不再”,但是,昌耀的《命運之書》和羅門的《時空奏鳴曲》仍能給我們帶來對詩的美好懷想。畢竟,詩歌的精神不會隨著物欲橫流的世界而偃旗息鼓,銷聲匿跡。
關(guān)于昌耀其人其詩,一些詩歌刊物和報紙的副刊曾把他哄抬到相當(dāng)高的高度。中國詩歌學(xué)會曾在醫(yī)院向病重的昌耀頒發(fā)了首屆年度詩歌獎的獎金和獎杯并稱其為“詩人中的詩人”;青海人民出版社也在他逝去后,破天荒地為這個苦難的西部歌者出版了一部豪華版的《昌耀詩文總集》,以此告慰詩人于九泉。而據(jù)我所知,在昌耀離去之后,有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青海的年輕愛詩者會利用各種場合議論他并且祭祀他,如把喝剩下的殘酒潑在狼藉的飯桌上,嘴里說幾句“大師安息”之類的醉話。說實在的,昌耀在我眼里不過是一個鄰居,一位同事,一個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的朋友。至少我認(rèn)為,他所從事的日常工作毫無詩意并且與詩歌毫不相干。比如,我每每看到的這位詩人總是穿一件類似糧油門市部工作人員所穿的那種藍(lán)布大褂,而且在他騎的那輛令他愛惜備至的自行車后捎盤上,從來都不缺少蘿卜青菜,米面油鹽。他穿藍(lán)色長衫是為了保護身上那件曾經(jīng)時髦過的灰顏色的“巴拿馬西服”,因為他要給他的三個孩子做飯,還要從煤房里往樓上搬運煤磚,而更多的時候他是在與老婆打架或與未成年的大兒子打架。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在做完了家務(wù)嘔夠了鳥氣之后長時間地把自己關(guān)在不足五平方米的所謂書房里,或去擺弄那臺使他愛不釋手的照相機,或去無人可知的想象世界里神游,并偶爾抒發(fā)一下他對苦難生話的追懷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那首《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比如《劃呀,劃呀,父親們!》,比如《古城:二十四部燈》等在國內(nèi)詩壇叫得響的作品,據(jù)他說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出世的。也許他不說誰也不會知道,在他躲在小屋里創(chuàng)造詩歌的時候,沒有暖氣的冬天在西寧是多么地寒冷。在他歌頌他的土伯特女人和三個孩子的時候,他的那扇只要放他進去就死也不會為他人打開的門,常常會被那個女人從外面踢破,門鎖也會被反鎖上,于是他只能在幾個空啤酒瓶里小便,在一條自制的土沙發(fā)上和衣而臥。正如他的詠嘆,正如那首《斯人》:靜極——誰的嘆噓?密西西比河此刻風(fēng)雨,在那邊攀緣而走。地球這壁,一人無語獨坐。……這樣的詩,這樣的的氣度與智慧,這樣的孤獨與憔悴,我敢說,沒人樂意同他分享。
昌耀用他的詩歌沒能把他的老婆孩子養(yǎng)活好,所以就無奈地毫無尊嚴(yán)地離家出走了。這個50多歲的被詩評家譽之為大師抑或圣手的男人,有一天突然感到了一種無可名狀的悲郁和暴怒,他想,自己非但沒能把老婆孩子養(yǎng)活好,同樣也沒能把自己養(yǎng)活好,于是就將平生所著詩文剪輯成冊,命題為《命運之書》并且在國內(nèi)多家報刊發(fā)出了一封致詩界朋友和讀者的公開信,聲明自己“因書稿屢試不驗”因此要“奮起自救”甚至要“圖窮而匕首見”了。此后他在《唐·吉訶德軍團還在前進》一詩中這樣自嘲道:“一路丟盔卸甲”、“吃盡皮肉之苦,遭到滿堂哄笑,累累如喪家之狗”……但所有這一切的發(fā)生,正如詩人所說:痛苦是常有的事,而最痛苦的唯有精神的缺席。
昌耀其人其詩讓我對詩、對人產(chǎn)生這樣的想法,就是說:你的一些美好雄奇的渴望和追求,如果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現(xiàn)不了,那么,你就在詩歌里想方設(shè)法去實現(xiàn)吧。如果你的生活很苦澀很沒意思,那么就讓自己的詩歌不苦澀甚至有一種桃花源般的浪漫與美妙。這就好像西北的花兒一樣,那么美妙那么動人那么有想象力的花兒,不都出自窮苦農(nóng)民之口嗎?
我與羅門先生的相識是在1988年的海口。當(dāng)時海南剛建省,而在此前短短幾個月里,據(jù)說有十萬所謂的大陸人才闖過瓊州海峽,在海口的秀英港和新港登岸,而其中就包括了許多已成名或未成名的青年詩人。成群結(jié)隊的詩人在海口大街上走來走去,一些號稱這派那派的所謂掌門人求職無門,居無定所。真正是人潮如涌,泥沙俱下。就是在這樣一種心浮氣躁的情形下,我有幸在一個臺風(fēng)登陸之夜,頂著十級大風(fēng),去海口賓
相關(guān)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
網(wǎng)友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