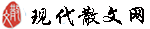我心目中的好散文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
雷 達
●任何文學、任何文體,都在“質文互變”中走著自己的路程,現在我們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質”沖破“舊文”的關頭了,從而建設新一代的質文平衡。
一
傳統的散文發展到今天,確乎愈益暴露出它與當代人精神脫節的疲憊,被文體定勢的重負壓得直不起腰,而其中最致命的,乃是思想的貧瘠,哲理的貧乏——無力洞察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饑渴。這大約與我們民族不是長于哲學思維有關。是的,倘若一個時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不能在散文中得到體現,倘若散文不能對時代和民族的靈魂狀態加以思考;倘若散文找不到富于時代感的思與詩的言說方式,那是沒有創新可言的。為此,我也曾提出過新散文必須解決的問題,即滲透現代人生意義的哲理思考;形而下與形而上的融匯——走向象征與超越;繼承傳統并轉化傳統,創造新的語匯、節奏、表述方式。散文的審美品格與思想品格同樣重要,不講究審美價值,可能混同于哲學、邏輯學、文化學,那是散文的另一歧途。散文必須首先是形象、意境直至有意味的形式。
我感興趣的散文,首先必須是活文、有生命之文,而非死文、呆文、繁縟之文、綺靡之文、矯飾之文。自從赫拉克利特說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的素樸真理以來,人類對于自身在流轉的大化中的感覺就重視起來,懂得運動感是一切有生命的活物的重要特征。我對散文也有依此而自設的標準,那就是看它是否來自運動著的現實,包含著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維的浪花是否采擷于湍急的時間之流,是否實踐主體的毛茸茸的鮮活感受。有些作家名重一時,甚至被尊為散文泰斗,其寫作方式似乎是,寫喝茶就搜羅關于茶的一切傳說軼聞,寫喝酒就陳述酒的歷史和趣聞,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識可謂淵博,用語可謂典雅——不知為什么,對這種考究的文章我始終提不起興趣,甚而推想它可在書齋中批量生產。對另一類矯飾、甜膩、充滿夸張的熱情的“抒情散文”我也興趣不大,它們的特征是,語言工巧、纖秾、綺麗,但文藻背后的“情”,則往往蒼白無力,似曾相識,是已有審美經驗和圖式的同義反復。它們沒有屬于自己獨有的直覺和體悟,因而也無創造性可言。我真正喜愛的,是潑辣、鮮活的感受,是剛健清新的創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決不重復的電光一閃。這當然只有豐富飽滿的主體才可能生發得出來。
這類散文的最強者,毫無疑問,是魯迅。無論讀《野草》、讀《朝花夕拾》、讀《紀念劉和珍君》、讀《為了忘卻的紀念》……那數不清的星斗般的篇什,到處都會遇到直接導源于生命和實踐的感悟,它們是一次性的,只有此人于此時此刻才能產生,因而反倒永遠地新穎,歷久而不褪色變味。所以,要論我的散文觀,那就是:雖然承認那有如后花園蓊郁樹林掩映下的一潭靜靜碧水似的散文也是一種美,甚至是淵博、靜默、神秘的美,但我并不欣賞;我推崇并神往的,是那有如林中的響箭、雪地的萌芽、余焰中的刀光、大河里的喧騰浪花式的散文,那是滿溢著生命活力和透示著鮮亮血色的美。這并非教人躁急、忙迫,去空洞地吶喊,而是平靜下的洶涌,冷峻中的激活,無聲處的緊張。
二
現在人們已經驚異地發現,在這經濟的喧騰年月和文學的蕭索時期里,散文竟然出人意料地交上了好運。在人們的記憶里,散文的命運似乎沒有特別地壞過,也沒有特別地好過,它實在太久地擔當著文壇上的配角。講起歷史來,它的歷史比誰都悠長而輝煌,一回到現實,它卻總是沒有氣力與小說抗衡。可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事情起了變化,散文的際遇來臨了。這倒不是說它要重溫正統或正宗的夢,而是說,在這大轉型的時代,它有可能獲得比平常更為豐碩的成果,完成自身大的轉折。散文“中興”的秘密藏在時代生活的深心。用直白的話說就是:急劇變動的生活賜給了散文一個千載難逢的機緣。今天人人都可能有大量新的發現,提供出比平時多得多的新鮮體驗,從而打破僵硬模式的束縛,創造出開放的、新穎的風格;就散文自身來說,由于它的自由不羈,它可能是目前最便于傾吐當代人復雜心聲的一種形式。日日更新的生活是根據,散文的形式特征是條件,兩相遇合,造成了散文迅速發展自己的空間。
然而,能否真正產生叩響當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優勢和藝術空間還不行,歸根結底還要看作者——精神個體有無足夠的感應能力和創新能力,擺脫傳統壓力的能力和辟創新境的能力。一句話,關鍵還在“說話人”身上。對散文創作來說,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筆,傳統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現出來,熟絡的老詞句就不請自來,雨中登山呀,海上日出呀,流連蒼松云海呀,憐惜小貓小狗呀……經典散文已經形成的固定視角,有其頑固性,生活被它們分解成條條塊塊,以致我們身在生活中,卻麻木不仁,只知循著它們提供的角度去收撿素材,剪輯生活,與它們符合的東西,我們能感應,對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東西,我們無動于衷。這是多么荒謬的迷誤啊。于是,生活的完整性、豐富性、原生性、流動性全都不見了。我們好像拿著一張網,鮮活的水和鮮活的魚全漏掉了,最后還是只剩下了手中的這張網。
怎么辦呢?我想到了一句話,叫做:“有什么話,說什么話。”這是胡適先生的名言。也許,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鮮活還原回來,這種極端的提示,或笨辦法,很能解決問題。難道不是嗎?難道強顏歡笑、故作豪語、溫柔敦厚、曲終奏雅之類,沒有給我們的散文涂夠濃厚的新古典主義顏色嗎?一個個像是穿著筆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從來不放屁也從不上廁所似的,連跌跤也要講究姿勢的優雅。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隱形規定似的。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氣沉沉、病病懨懨的委靡相呢?不來點自然主義的恣肆,不光著泥腿子踏進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喚起散文的活力的。“有什么話,說什么話”意味著不顧原先說話的姿態、腔調、規范,只遵從心靈的呼喊,這就有可能說出新話、真話、驚世駭俗的話、“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實話,以及人人皆領受到了,卻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揭穿其底蘊的深刻的話。任何文學、任何文體,都在“質文互變”中走著自己的路程,現在我們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質”沖破“舊文”的關頭了,從而建設新一代的質文平衡。
三
看賈平凹的《說話》,至少要讓你一愣:連“說話”這樣習焉不察的事也可寫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顧散文的體式,不顧開端呀,照應呀,結尾的升華呀,有無意義呀,真是太大膽也太放縱了,真是只講過程,不問意義,到處有生活,撿到籃里都是菜。據說,《說話》是平凹在北京開政協會議期間接受約稿,在一張信紙上隨手一氣寫下來的。為什么想到說話問題了?大約一到北京,八面應酬,拙于言辭的賈氏發現說話成了大問題,才有感而發的吧。這篇東西是天籟之音,人籟之聲,極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絕了硬做的痕跡,里面的幽默、機智、無奈,都是生活與心靈自身就有的,無須外加,渾然天成,可謂“有什么話,說什么話”的最佳實踐。
所謂“有什么話,說什么話”,并非漫無邊際的胡侃。大街流氓的爆粗口和小巷潑婦的海罵,倒也是“有什么話,說什么話”,那能成為好散文嗎?冬烘先生的喃喃,滿嘴套話的豪言,那能成為好散文嗎?“有什么話,說什么話”的精義,全在于自由、本真、誠摯、無畏。我一向認為,精于權術,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嚴嚴的,面部肌肉擅長阿諛,卻喪失了大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寫出好散文的。他經商,會財源滾滾;他從政,會扶搖直上;他整人,會口蜜腹劍;他戀愛,會巧舌如簧;他治學,會偷梁換柱;他偶爾也會“幽默”一下,結果弄得大家鴉雀無聲。他在很多領域都會成功,唯獨寫不出一篇好散文。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過來說天道畢竟公正?
提倡“有什么話,說什么話”,并不排斥開掘、提煉、升華的重要。我們常說散文要有真情實感,原本不錯的,但關鍵要看是什么水準的真情實感,從怎樣的主體生發出來的怎樣的真情實感。牛漢的《父親、樹林和鳥》,不是飽經憂患且充滿悲劇感者,斷然寫不出來。感情濃到化不開,重到承受不起時,才產生了這樣簡潔、飽滿、幽咽、滯澀的聲音。父親說了:“鳥最快活的時刻,向天空飛離樹枝的一瞬間,最容易被獵人打中。”為什么呢?因為“黎明時的鳥,翅膀濕重,飛起來沉重”。作者慶幸于“父親不是獵人”,可是獵人卻大有人在啊。作者對生命的美麗和因其美麗而帶來的脆弱,滿懷憂傷。那意思是說,純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純真的生命是不設防的,惟其純真,惟其快活,就特別容易遭到踐踏、傷害和暗算。作者其實是在為天真、善良、單純的美唱一支憂心的歌啊。多么質樸的畫面,多么深沉的感懷!作者還寫過一篇《早熟的棗子》,也是寄托遙深,他說,在滿樹青棗中,只有一顆紅得刺眼,紅得傷心,那是因為“被蟲咬了心”,一夜之間由青變紅,倉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作者說,他憎恨這悲哀的早熟,而寧可羨慕綠色的青澀,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四
散文的魅力說到底,乃是一種人格魅力的直呈。主體的境界決定著散文的境界。我也寫散文,也想向我心儀的目標努力,卻收效甚微。我寫散文,完全是緣情而起,隨興所至,興來弄筆,興未盡而筆已歇,沒有什么宏遠目標,也沒有什么刻意追求,于是零零落落,不成陣勢。我寫散文,創作的因素較弱,傾吐的欲望很強,如與友人雪夜盤膝對談,如給情人寫的信札,如郁悶日久、忽然沖喉而出的歌聲,因而顧不上推敲,有時還把自己性格的弱點一并暴露了。蒙田的一段話,竟好像是為我而說的:“如果我希求世界的贊賞,我就會用心修飾自己,仔細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見。我要人們在這里看見我的平凡、純樸和天然的生活,無拘束亦無造作,因為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有一天,我遠離了我的朋友,他們重新打開這些散文,將會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張頑皮的笑臉。
其實,我寫的并不單是我,我寫的是一種生存相,一種精神狀態,一種也許無望的追求。我早就發現,這年月自我感覺良好的人越來越多,無論是商海豪杰還是文化英雄,而我,不知為什么,自我感覺始終好不起來,心緒總是沉甸甸的,我懷疑我是否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逸民。我背負著傳統的包袱,卻生活在一個高度縮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質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狀態,清新的感覺,蠻勇的體魄,文明的情懷而不可得,有時我想,當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點以后,我是否該逃到我的大西北故鄉去流浪,這么想著的時候,便也常常感受著一種莫名的悲哀。
當我奔波在還鄉的土路上,當我觀看世界杯足球賽熬過一個個深宵,當我跳入刺骨的冰水,當我踏進域外的教堂,當我佇立在皋蘭山之巔仰觀滿天星斗,當我的耳畔回蕩著悲涼慷慨的秦腔,我便是在用我的生命與冷漠而喧囂的存在肉搏,多么希望體驗人性復歸的滿溢境界。可惜,這只是一種癡念。優美的瞬間轉眼消失,剩下的是我和一個廣大的物化世界。
相關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
網友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