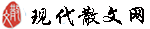弋舟:到世界去
弋舟:到世界去
編者按:近日,備受文壇矚目的2020收獲文學(xué)榜公布榜單,短篇小說(shuō)排行榜中,陜西作家弋舟《人類的算法》入榜。
文學(xué)陝軍藉此機(jī)會(huì),得以對(duì)話平日沉浸于寫作世界的作家弋舟,與他暢談《人類的算法》的自評(píng)、文學(xué)對(duì)于“人的困境”的意義、如何破解地域性書寫的拘囿,以及短篇小說(shuō)的“輕重”等話題。
弋舟的文學(xué)世界,自成一個(gè)龐大的語(yǔ)境,以作品上榜為契機(jī)的一次簡(jiǎn)略采訪,我們視為弋舟系列報(bào)道的初始。弋舟新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正在創(chuàng)作中,文學(xué)陝軍對(duì)陜西作家取得的成績(jī)、榮譽(yù),也將以“長(zhǎng)篇”的方式,連續(xù)地、系列地關(guān)注下去。
文學(xué)陝軍:弋舟老師您好,日前,《收獲》雜志公布了“2020收獲文學(xué)榜”上榜作品名單,您發(fā)表于《野草》2020年第2期的《人類的算法》登上短篇小說(shuō)榜。《收獲》作為國(guó)內(nèi)重要的文學(xué)期刊,已成功舉辦五屆“收獲文學(xué)榜”,這是您第三次上榜。作為作者,如何自評(píng)您的《人類的算法》?
弋舟:《收獲》是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壇的重要陣地,60多年來(lái),她刊發(fā)了大量重要、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素有“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簡(jiǎn)史”的美譽(yù)。2016年,由《收獲》牽頭的年度文學(xué)排行榜創(chuàng)辦,基于她的文壇公信力與地位,這個(gè)排行榜迅速以其權(quán)威、多元、公正與客觀在海內(nèi)外聚集起重要影響,成為透析當(dāng)代中國(guó)文學(xué)的重要依據(jù)和“矢量圖”。
榮幸的是,在首屆“收獲文學(xué)榜”中,我的短篇小說(shuō)《隨園》便登上了短篇小說(shuō)“專家榜”與“讀者榜”的雙榜首。對(duì)于一個(gè)寫作者而言,這無(wú)疑是莫大的肯定與榮譽(yù)。2018年,第四屆“收獲文學(xué)榜”中,我的短篇小說(shuō)《核桃樹下金銀花》再次上榜,加上今年的《人類的算法》登上第五屆“收獲文學(xué)榜”,我上榜三次,對(duì)我而言,這是寫作生涯重要的成績(jī),加之平凹老師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也屢屢登榜,這樣的收獲,也可視為我們文學(xué)陜軍在全國(guó)文壇一份重要的成績(jī)與收獲。
《人類的算法》寫于年初疫情最為嚴(yán)峻的時(shí)刻,彼時(shí)“算法”成為了我們關(guān)注疫情、乃至防疫的重要技術(shù)手段,同時(shí),技術(shù)的進(jìn)步也一并帶來(lái)了新的精神困境——生而為人,我們終究難以屈從自己僅僅是一個(gè)個(gè)抽象的數(shù)據(jù)。基于此,我寫下了這個(gè)短篇。小說(shuō)依舊從平凡者的世俗生活入手,而我試圖探討的,依然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復(fù)雜性與每一個(gè)生命擁有者的心靈難度。當(dāng)我嘗試著將一個(gè)具體而微的女性與浩大的“人類算法”相互映照時(shí),我看到了生命個(gè)體在歷經(jīng)艱難之后所能達(dá)到的寬宥與平靜,至少,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dāng)我們把個(gè)體的命運(yùn)置放在人類的背景中時(shí),我們能夠獲得某種安慰。
小說(shuō)發(fā)表于《野草》雜志,這本刊物是魯迅先生故鄉(xiāng)的刊物,我自己也一度受聘為紹興市的“駐城作家”,所以,這個(gè)短篇也算是我交出的一份作業(yè)。小說(shuō)發(fā)表后,《小說(shuō)月報(bào)》《中華文學(xué)選刊》均有轉(zhuǎn)載,算是擴(kuò)大了讀者面,而《收獲》這本刊物與巴金先生的名字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把心交給讀者”,是巴金先生最為著名的文學(xué)囑咐,在這個(gè)意義上,我也很高興這些刊物能夠讓我的小說(shuō)與更多的讀者達(dá)成共鳴。
文學(xué)陝軍:《人類的算法》寫于2020年春節(jié)后,《掩面時(shí)分》、《羊群過(guò)境》,它們都與“人的困境”有關(guān)。您在2020年出版的《庚子故事集》這個(gè)主題,也是從《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貫之下來(lái)的。關(guān)于“人的困境”主題,今年全人類的集體感受尤為強(qiáng)烈,作為作家,您認(rèn)為文學(xué)對(duì)“人的困境”的命題,“解釋”與“撫慰”的作用幾何?
弋舟:我從事著這份工作,當(dāng)然會(huì)確信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人的困境”一定不會(huì)是一個(gè)偽命題,否則我們就無(wú)從渴望進(jìn)步,而所謂進(jìn)步,也一定不僅僅限于我們對(duì)物質(zhì)世界的改造,毋寧說(shuō),人類的進(jìn)步之路,最終是以精神世界的解放為目的的。那么,指出我們的困境所在,體恤人的靈魂,甚至嘗試著給出一些方案,這些重大的命題,都成為了文學(xué)得以存在的前提。一個(gè)運(yùn)動(dòng)員如何跑得快,文學(xué)不太插得上手,那個(gè)要交給教練員,文學(xué)能夠幫上忙的,是運(yùn)動(dòng)員跑不快的時(shí)候,她會(huì)試著撫慰、試著加油、試著告訴你:跑不快也不是天大的罪過(guò),因?yàn)樯鵀槿耍憔陀腥说南薅取?/p>
文學(xué)陝軍:對(duì)于短篇小說(shuō)寫作,您是有話語(yǔ)權(quán)的,以短篇小說(shuō)《出警》獲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著有五部短篇小說(shuō)集,還寫有“新批評(píng)”系列文章論“短篇小說(shuō)的稱重”,對(duì)于短篇小說(shuō)的寫作,你認(rèn)為它的“輕”與“重”可有平衡把握的“秘訣”?
弋舟:話語(yǔ)權(quán)一定是沒有的,而且我也懷疑這個(gè)權(quán)真的會(huì)被誰(shuí)擁有。雖然我擔(dān)任著省作協(xié)中短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委員會(huì)的副主任,我也只是作為一個(gè)寫作者給出自己對(duì)于這門藝術(shù)的粗淺理解。短篇小說(shuō)的“輕”與“重”,其實(shí)不過(guò)關(guān)乎著寫作者自身對(duì)于世界認(rèn)知的“輕”與“重”,如何平衡,本身就是對(duì)于寫作者世界觀的考量。如果這里有“秘訣”而言,那就是我們的“三觀”直接在此得以表達(dá),你面對(duì)世界的時(shí)候不知道輕重,你也將無(wú)從理解短篇小說(shuō)的輕與重。
文學(xué)陝軍:“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guān)中……當(dāng)這一連串的地理坐標(biāo)排列于紙面,熟悉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你,一定會(huì)在瞬間喚醒自己那頑固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您在《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一文中關(guān)注“拘囿”與“掙脫”的問(wèn)題,既點(diǎn)明了地方性書寫的困局,也努力嘗試著開辟新的路徑。在您看來(lái),作家寫作中的“必須”性,導(dǎo)致了目前地方性書寫的套路化。而真正的寫作,其實(shí)因?yàn)?ldquo;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所以才能煥發(fā)出“西西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虛妄的勇氣”。這種勇氣,終將令作家“張望到了自由”。擺脫地方性寫作的拘囿,它的路徑在哪?
弋舟:到世界去。這個(gè)“到世界去”,也許更多地是在描述一種精神性的流浪,有些人兩腳跑出了萬(wàn)里,靈魂不過(guò)依然關(guān)在自家的窯洞中。沒有“世界”作為映照,“故鄉(xiāng)”的意義也會(huì)闕如。我們都有過(guò)類似的經(jīng)驗(yàn):自己的故鄉(xiāng)看在自己眼里,一定與一個(gè)游客眼中的感受是不同的,沒有那么美,或者沒有那么糟糕,同樣,當(dāng)我們?nèi)ネ怂l(xiāng),也將收獲到不同于當(dāng)?shù)厝说慕?jīng)驗(yàn)。這種現(xiàn)象只說(shuō)明了“流浪”對(duì)于新的經(jīng)驗(yàn)的重要性。主體性的建立,是需要依賴他者作為參照物的。靈魂的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都是致命的牢籠。
文學(xué)陝軍:很多外地記者對(duì)您似乎有一種“共識(shí)”——相對(duì)其他陜西作家,你的作品似乎多了些南方氣質(zhì)。您對(duì)此的解釋是:“如果當(dāng)真如此,只能歸結(jié)于血脈深處那些玄奧的基因了。”
您祖籍江蘇,在西安成長(zhǎng),后長(zhǎng)居蘭州,現(xiàn)在又回到西安。您常說(shuō)自己是沒有故鄉(xiāng)的“異鄉(xiāng)人”,西安的古城墻和一毛錢一碗的岐山臊子面,是童年精神和物質(zhì)的雙重記憶,還有那個(gè)希望與絕望同行、文化與思想碰撞的70年代生人的成長(zhǎng)史。成長(zhǎng)史對(duì)您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意味著什么?
弋舟:這份簡(jiǎn)歷聽上去好像很復(fù)雜,其實(shí)復(fù)雜一些也未嘗不好,曲折往復(fù),本身就構(gòu)成“經(jīng)驗(yàn)”。在這個(gè)意義上,你也可以將我的“成長(zhǎng)史”視為“流浪史”,而精神的流浪,我已經(jīng)說(shuō)過(guò),對(duì)于一個(gè)寫作者而言是重要且寶貴的。
然而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我的經(jīng)歷似乎也未見得有多么的復(fù)雜,生逢此世,每一個(gè)中國(guó)人都感受著時(shí)代的宏力,我們的一切經(jīng)驗(yàn),都受制于時(shí)代的洪流。
文學(xué)陝軍:在《美文》雜志上讀到您的系列專欄“春臨”,對(duì)于各地的行走及感觸,您進(jìn)行了專欄式書寫,踐行著“讀萬(wàn)卷書,行萬(wàn)里路”,2021年您的“春臨”專欄從內(nèi)文“升級(jí)”為封三,還配了您的畫作,行走、書畫一體,是您的遣興一種,還是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學(xué)化表達(dá)?
弋舟:《美文》是我們陜西在全國(guó)具有影響力的刊物之一,受邀寫專欄,當(dāng)然是我的榮譽(yù)。“春臨”這個(gè)詞,是平凹先生題贈(zèng)我的,也是我現(xiàn)在居住的地名,用它來(lái)做專欄的名字,對(duì)我而言,美意別具。散文這種文體在表達(dá)“讀萬(wàn)卷書,行萬(wàn)里路”的感受上優(yōu)勢(shì)突出,以此來(lái)平衡自己的感性與理性,對(duì)我都是重要的訓(xùn)練。
至于“升級(jí)”,的確就是勉為其難的事了。我只能感謝《美文》的抬愛與鞭策。你說(shuō)得不錯(cuò),這樣的方式更接近于一種“生活方式”了,是遣興,也是文化表達(dá),重要的也許還在于,這是一個(gè)機(jī)會(huì),令我將工作與活著本身更為圓融地貫通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修煉——我怎么寫就怎么生,我怎么畫,就怎么活。
文學(xué)陝軍:您著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跛足之年》《蝌蚪》《戰(zhàn)事》《春秋誤》《我們的踟躕》,對(duì)于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寫作,2021年可有意向和規(guī)劃?
弋舟:已經(jīng)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寫作計(jì)劃在展開了。2020年我簽約了“十月文學(xué)院”,這其中就包含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約定。很高興,此次簽約的作家中還有我們的“鄉(xiāng)黨”陳彥先生,我也期待自己能寫出不被鄉(xiāng)黨笑話的作品。
文學(xué)陝軍: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祝您的創(chuàng)作有更大的“收獲”!
弋舟:謝謝。“文學(xué)陝軍”是我們作協(xié)重要的平臺(tái),你們辛苦了,也祝愿你們?cè)谛碌囊?/p>
相關(guān)閱讀:
|
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
網(wǎng)友評(píng)論(共有 0 條評(píng)論) |
散文信息
| 著名作家財(cái)神 | 孫犁的意義 | 首屆“絲路散 | 陜西散文界新 | ||||
| 陜西6位作家獲 | 賈平凹:散文 | “孫犁文學(xué)獎(jiǎng) | 解晚晴美文集 | ||||
| 恕我直言--不 | 詩(shī)性美文中的 | 散文的尷尬 | 自然散文的意 |